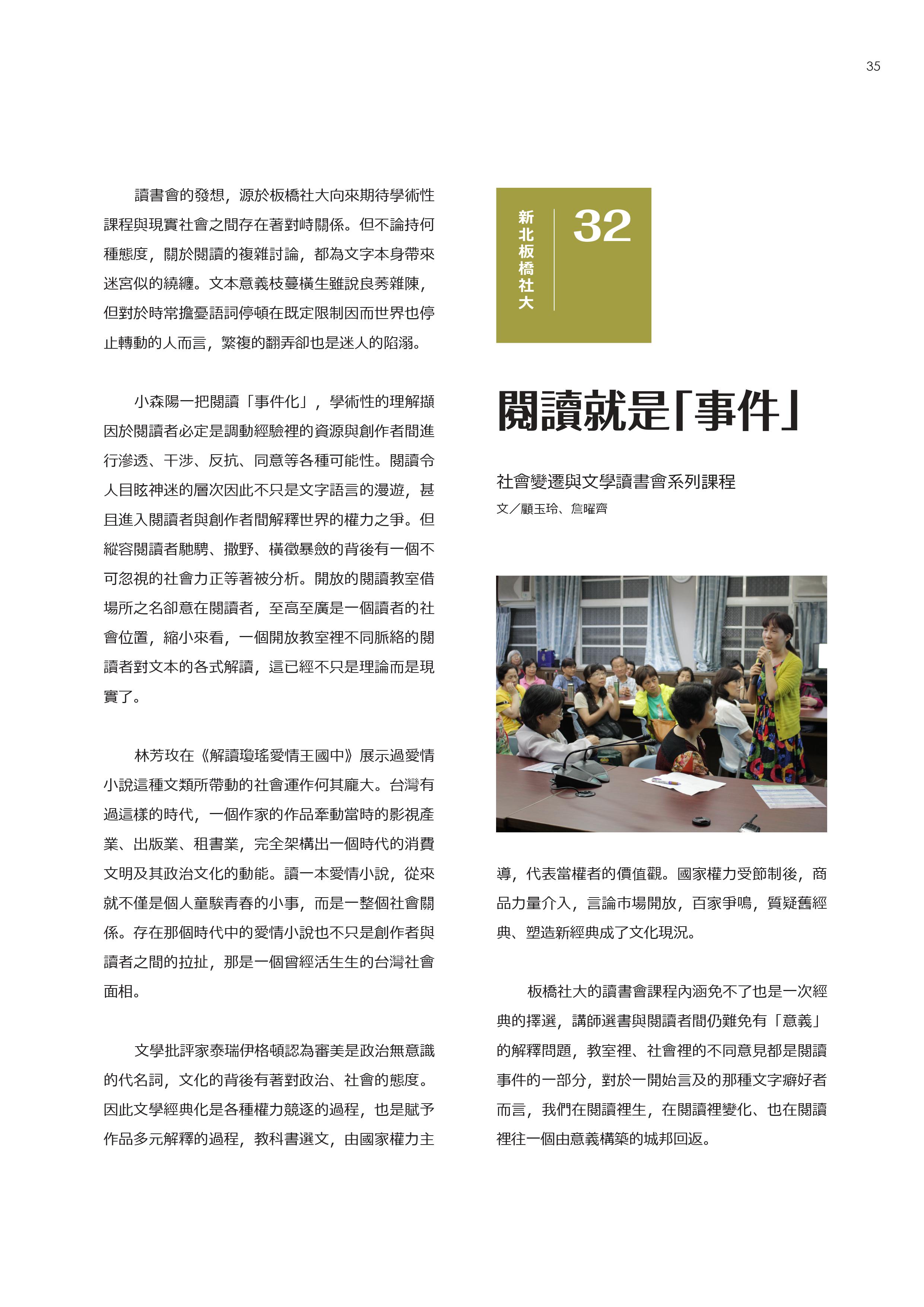讀書會的發想,源於板橋社大向來期待學術性課程與現實社會之間存在著對峙關係。但不論持何種態度,關於閱讀的複雜討論,都為文字本身帶來迷宮似的繞纏。文本意義枝蔓橫生雖說良莠雜陳,但對於時常擔憂語詞停頓在既定限制因而世界也停止轉動的人而言,繁複的翻弄卻也是迷人的陷溺。
小森陽一把閱讀「事件化」,學術性的理解擷因於閱讀者必定是調動經驗裡的資源與創作者間進行滲透、干涉、反抗、同意等各種可能性。閱讀令人目眩神迷的層次因此不只是文字語言的漫遊,甚且進入閱讀者與創作者間解釋世界的權力之爭。但縱容閱讀者馳騁、撒野、橫徵暴斂的背後有一個不可忽視的社會力正等著被分析。開放的閱讀教室借場所之名卻意在閱讀者,至高至廣是一個讀者的社會位置,縮小來看,一個開放教室裡不同脈絡的閱讀者對文本的各式解讀,這已經不只是理論而是現實了。
林芳玫在《解讀瓊瑤愛情王國中》展示過愛情小說這種文類所帶動的社會運作何其龐大。台灣有過這樣的時代,一個作家的作品牽動當時的影視產業、出版業、租書業,完全架構出一個時代的消費文明及其政治文化的動能。讀一本愛情小說,從來就不僅是個人童騃青春的小事,而是一整個社會關係。存在那個時代中的愛情小說也不只是創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拉扯,那是一個曾經活生生的台灣社會面相。
文學批評家泰瑞伊格頓認為審美是政治無意識的代名詞,文化的背後有著對政治、社會的態度。因此文學經典化是各種權力競逐的過程,也是賦予作品多元解釋的過程,教科書選文,由國家權力主導,代表當權者的價值觀。國家權力受節制後,商品力量介入,言論市場開放,百家爭鳴,質疑舊經典、塑造新經典成了文化現況。
板橋社大的讀書會課程內涵免不了也是一次經典的擇選,講師選書與閱讀者間仍難免有「意義」的解釋問題,教室裡、社會裡的不同意見都是閱讀事件的一部分,對於一開始言及的那種文字癖好者而言,我們在閱讀裡生,在閱讀裡變化、也在閱讀裡往一個由意義構築的城邦回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