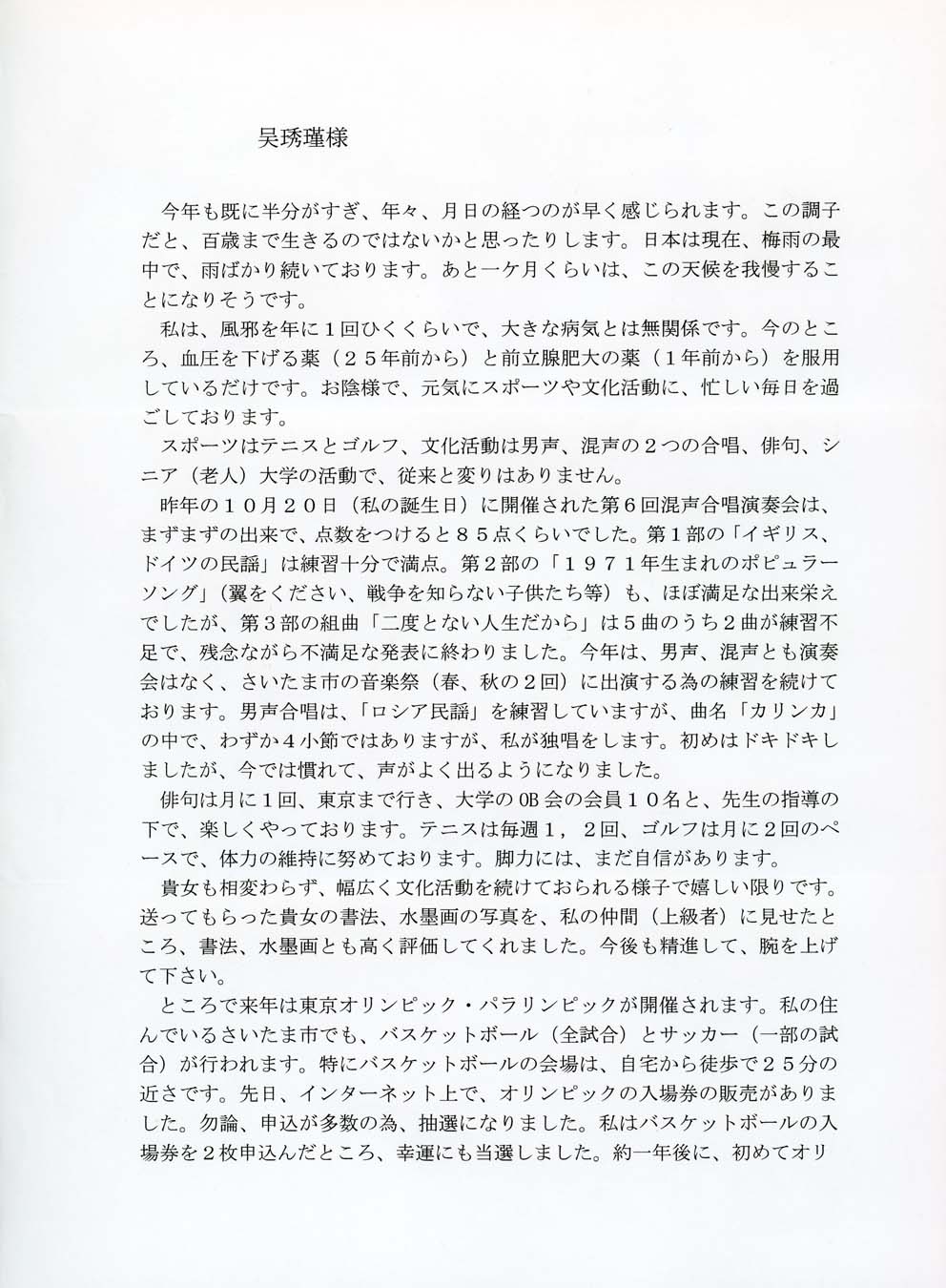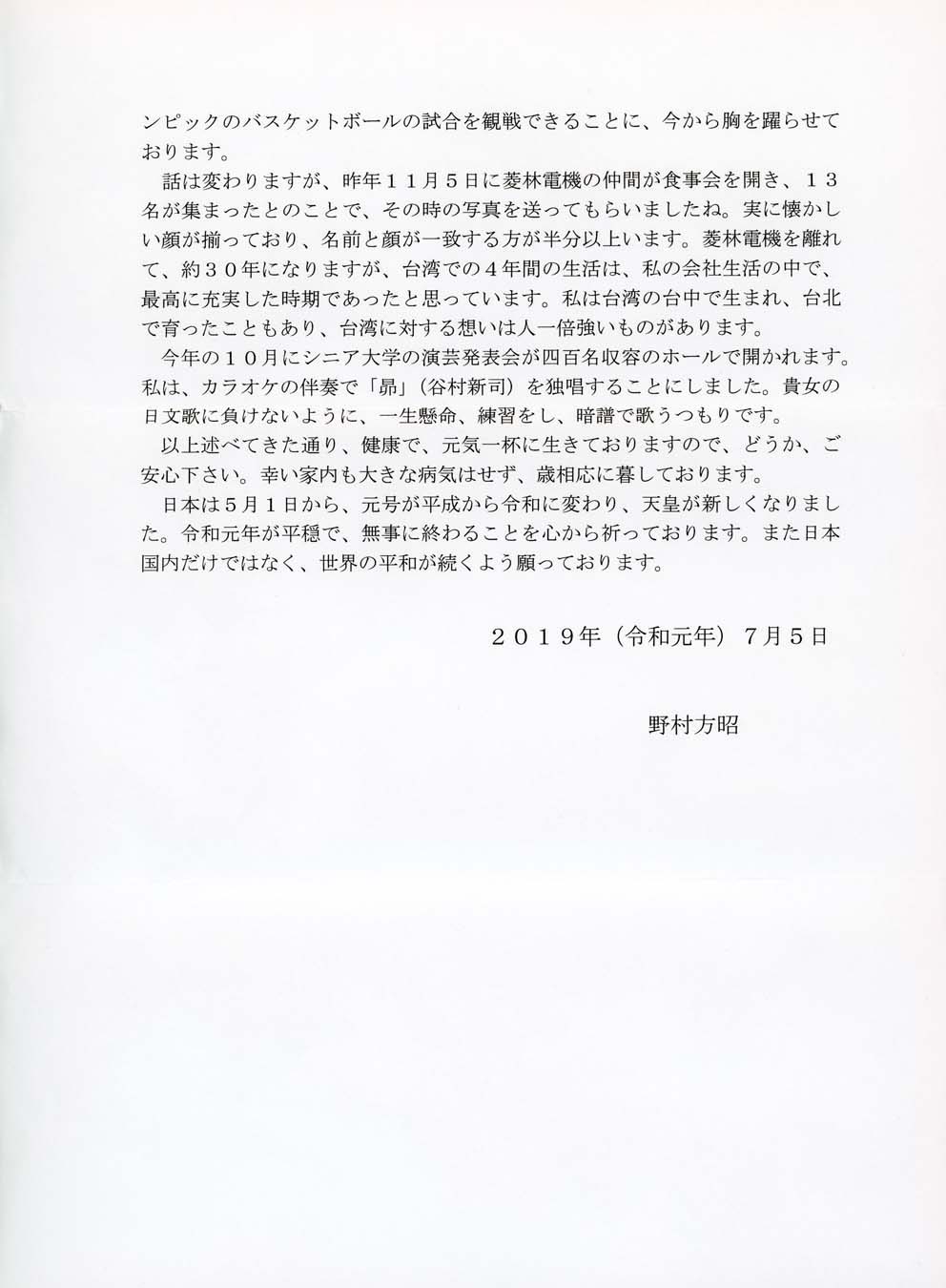野村先生是日本時期在臺灣出生的日本人,戰後隨著家人被遣返日本國內,在臺灣經濟發展之時,野村帶著兒時的想念再度回到台灣工作,但隨著台日合作關係的結束又被調回日本。野村持續與台灣前同事吳秀瑾保持二十幾年的通信,從不間斷,從信件中更能了解移民生活的各個面向。
這封信是野村先生最近的一封信,也是日本令和元年寫的一封信。隨著年齡越來越大,也隨著回到日本的時間越來越久,野村先生在前幾封信中開始說,自己的中文恐怕快要遺忘光了。這是帶有悲傷的說法,遺忘了一種自己半生工作地點的語言,幾乎就等於要遺忘自己的人生一半的重要文化。但這不是有意的遺忘,而是一種使用的失去彈性,也是一個人隨著年紀就會慢慢出現的狀態。野村先生一方面依舊持續地說著他這一年的生活重心,一方面說著,自己希望還有機會可到台灣看看。對於一個移民者來說,尤其文化上的累積總是會在不同的時刻呈現出來,但也可能會遺忘一些看起來很基本的技能,例如文字或語言。但就些都是外在學習而來的,野村先生談到中文慢慢離他而去,應該也是一種對記憶難以掌握的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