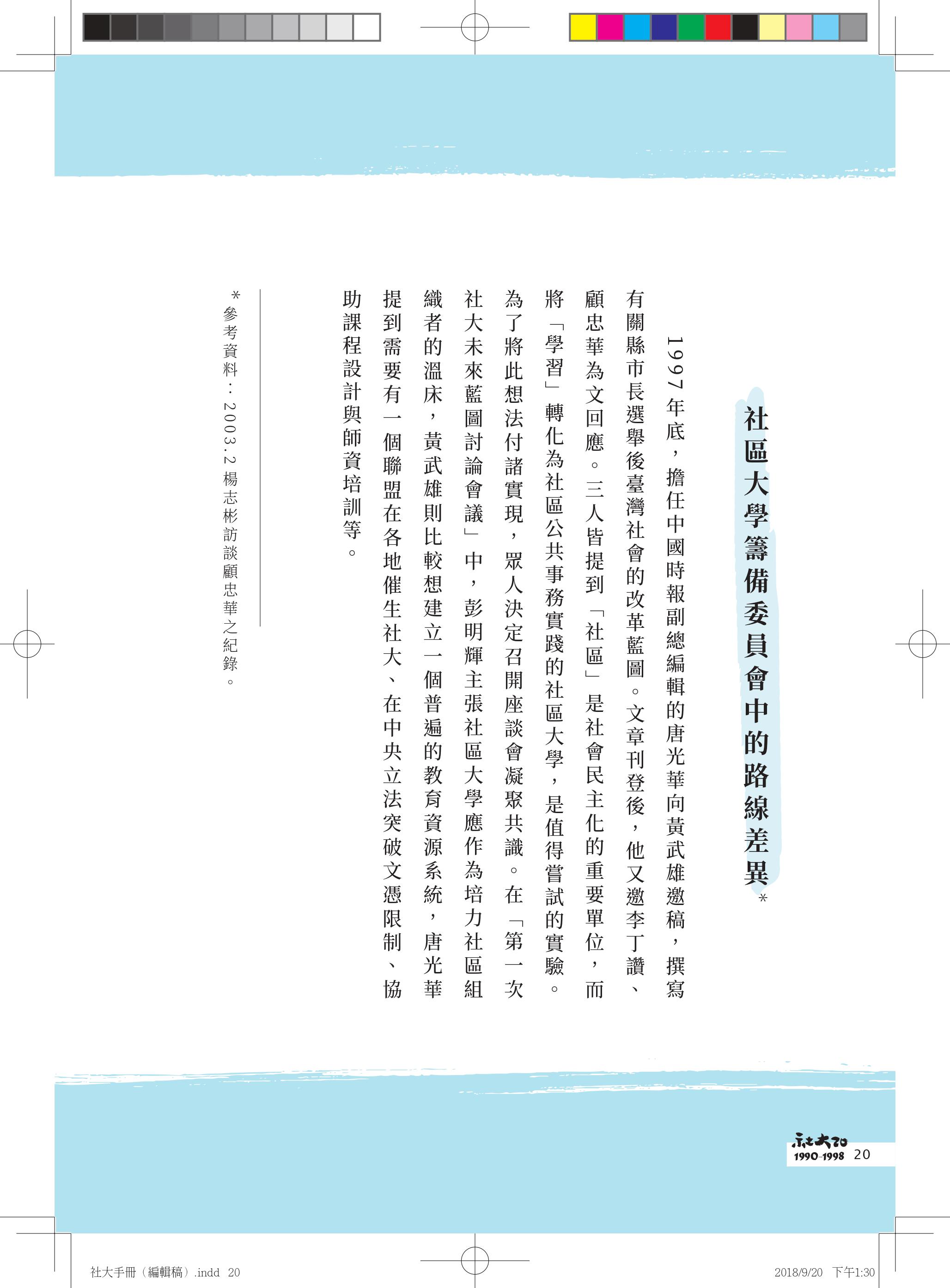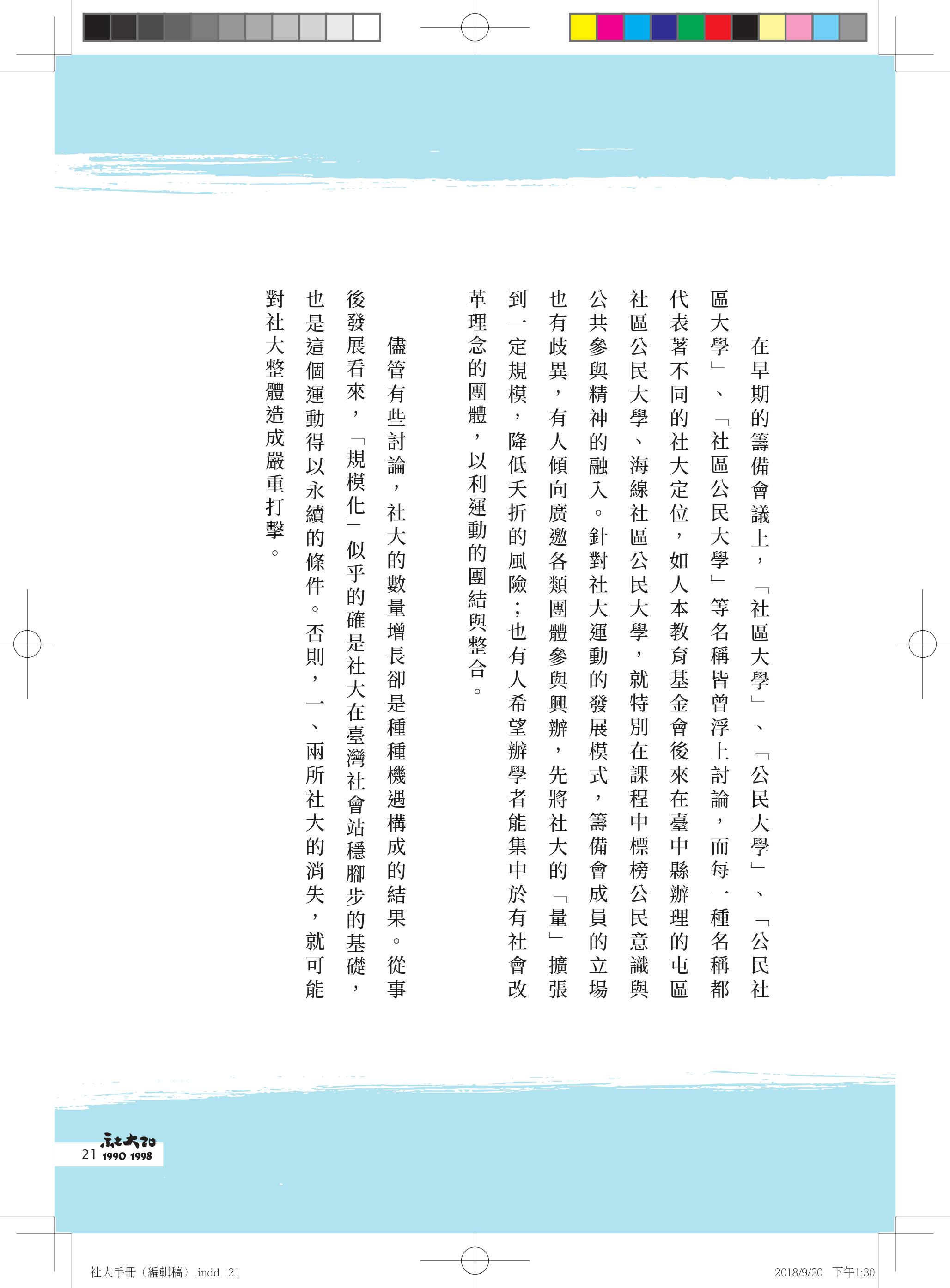1997年底,擔任中國時報副總編輯的唐光華向黃武雄邀稿,撰寫有關縣市長選舉後台灣社會的改革藍圖。文章刊登後,他又邀顧忠華為文回應。兩人皆提到「社區」是社會民主化的重要單位,而將「學習」轉化為社區公共事務實踐的社區大學,是值得嘗試的實驗。為了將此想法付諸實現,眾人決定召開座談會凝聚共識。在「第一次社大未來藍圖討論會議」中,彭明輝主張社區大學應作為培力社區組織者的溫床,黃武雄則比較想建立一個普遍的教育資源系統,唐光華提到需要有一個聯盟在各地催生社大、在中央立法突破文憑限制、協助課程設計與師資培訓等。
在早期的籌備會議上,「社區大學」、「公民大學」、「公民社區大學」、「社區公民大學」等名稱皆曾浮上討論,而每一種名稱都代表著不同的社大定位,如人本教育基金會後來在台中縣辦理的屯區社區公民大學、海線社區公民大學,就特別在課程中標榜公民意識與公共參與精神的融入。針對社大運動的發展模式,籌備會成員的立場也有歧異,有人傾向廣邀各類團體參與興辦,先將社大的「量」擴張到一定規模,降低夭折的風險;也有人希望辦學者能集中於有社會改革理念的團體,以利運動的團結與整合。
儘管有些討論,社大的數量增長卻是種種機遇構成的結果。從事後發展看來,「規模化」似乎的確是社大在台灣社會站穩腳步的基礎,也是這個運動得以永續的條件。否則,一、兩所社大的消失,就可能對社大整體造成嚴重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