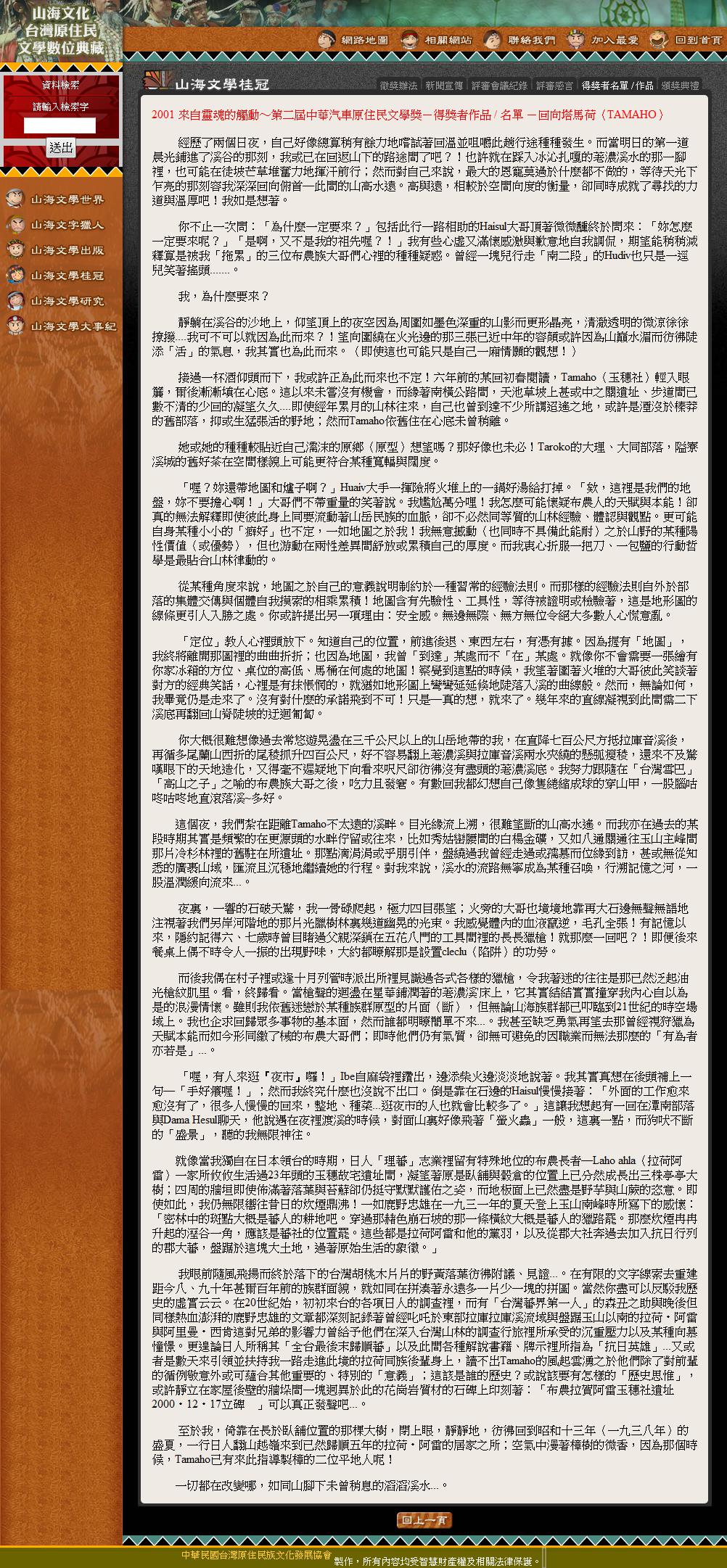跳到主要內容區塊
:::
山海文化 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
山海文化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資料檢索請輸入檢索字2001來自靈魂的觸動~第二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得獎者作品/名單-回向塔馬荷(TAMAHO) 經歷了兩個日夜,自己好像總算稍有餘力地嚐試著回溫並咀嚼此趟行途種種發生。而當明日的第一道晨光鋪進了溪谷的那刻,我或已在回返山下的路途間了吧?!也許就在踩入冰沁扎嘎的荖濃溪水的那一腳裡,也可能在徒坡芒草堆奮力地揮汗前行;然而對自己來說,最大的恩寵莫過於什麼都不做的,等待天光下乍亮的那刻容我深深回向俯首—此間的山高水遠。高與遠,相較於空間向度的衡量,卻同時成就了尋找的力道與溫厚吧!我如是想著。 你不止一次問:「為什麼一定要來?」包括此行一路相助的Haisul大哥頂著微微醺終於問來:「妳怎麼一定要來呢?」「是啊,又不是我的祖先喔?!」我有些心虛又滿懷感激與歉意地自我調侃,期望能稍稍減釋算是被我「拖累」的三位布農族大哥們心裡的種種疑惑。曾經一塊兒行走「南二段」的Hudiv也只是一逕兒笑著搖頭.......。 我,為什麼要來? 靜躺在溪谷的沙地上,仰望頂上的夜空因為周圍如墨色深重的山影而更形晶亮,清澈透明的微涼徐徐撩撥....我可不可以就因為此而來?!望向圍繞在火光邊的那三張已近中年的容顏或許因為山巔水湄而彷彿陡添「活」的氣息,我其實也為此而來。(即使這也可能只是自己一廂情願的觀想!) 接過一杯酒仰頭而下,我或許正為此而來也不定!六年前的某回初春閱讀,Tamaho(玉穗社)輕入眼簾,爾後漸漸填在心底。這以來未嘗沒有機會,而緣著南橫公路間,天池草坡上甚或中之關遺址、步道間已數不清的少回的凝望久久....即使經年累月的山林往來,自己也曾到達不少所謂迢遙之地,或許是湮沒於榛莽的舊部落,抑或生猛張活的野地;然而Tamaho依舊住在心底未曾稍離。 她或她的種種較貼近自己濡沫的原鄉(原型)想望嗎?那好像也未必!Taroko的大理、大同部落,隘寮溪城的舊好茶在空間樣貌上可能更符合某種寬輻與闊度。 「喔?妳還帶地圖和爐子啊?」Huaiv大手一揮險將火堆上的一鍋好湯給打掉。「欸,這裡是我們的地盤,妳不要擔心啊!」大哥們不帶重量的笑著說。我尷尬萬分哩!我怎麼可能懷疑布農人的天賦與本能!卻真的無法解釋即使彼此身上同要流動著山岳民族的血脈,卻不必然同等質的山林經驗、體認與觀點。更可能自身某種小小的「癖好」也不定,一如地圖之於我!我無意撼動(也同時不具備此能耐)之於山野的某種陽性價值(或優勢),但也游動在兩性差異間舒放或累積自己的厚度。而我衷心折服一把刀、一包鹽的行動哲學是最貼合山林律動的。 從某種角度來說,地圖之於自己的意義說明制約於一種習常的經驗法則。而那樣的經驗法則自外於部落的集體交傳與個體自我摸索的相乘累積!地圖含有先驗性、工具性,等待被證明或檢驗著,這是地形圖的線條更引人入勝之處。你或許提出另一項理由:安全感。無邊無際、無方無位令絕大多數人心慌意亂。 「定位」教人心裡頭放下。知道自己的位置,前進後退、東西左右,有憑有據。因為握有「地圖」,我終將離開那圖裡的曲曲折折;也因為地圖,我曾「到達」某處而不「在」某處。就像你不會需要一張繪有你家冰箱的方位、桌位的高低、馬桶在何處的地圖!察覺到這點的時候,我望著圍著火堆的大哥彼此笑談著對方的經典笑話,心裡是有抹悵惘的,就猶如地形圖上彎彎延延倏地陡落入溪的曲線般。然而,無論如何,我畢竟仍是走來了。沒有對什麼的承諾飛到不可!只是—真的想,就來了。幾年來的直線凝視到此間需二下溪底再翻回山脊陡坡的迂迴匍匐。 你大概很難想像過去常悠遊晃盪在三千公尺以上的山岳地帶的我,在直降七百公尺方抵拉庫音溪後,再循多尾蘭山西折的尾稜抓升四百公尺,好不容易翻上荖濃溪與拉庫音溪兩水夾繞的懸弧瘦稜,還來不及驚嘆眼下的天地造化,又得毫不遲疑地下向看來呎尺卻彷彿沒有盡頭的荖濃溪底。我努力跟隨在「台灣雪巴」「高山之子」之喻的布農族大哥之後,吃力且發窘。有數回我都幻想自己像隻綣縮成球的穿山甲,一股腦咕咚咕咚地直滾落溪~多好。 這個夜,我們紮在距離Tamaho不太遠的溪畔。目光緣流上溯,很難望斷的山高水遙。而我亦在過去的某段時期其實是頻繁的在更源頭的水畔佇留或往來,比如秀姑巒腰間的白楊金礦,又如八通關通往玉山主峰間那片冷杉林裡的舊駐在所遺址。那點滴涓涓或乎朋引伴,盤繞過我曾經走過或孺慕而位緣到訪,甚或無從知悉的廣裹山域,匯流且沉穩地繼續她的行程。對我來說,溪水的流路無寧成為某種召喚,行溯記憶之河,一股溫潤緩向流來...。 夜裏,一響的石破天驚,我一骨碌爬起,極力四目張望;火旁的大哥也境境地靠再大石邊無聲無語地注視著我們另岸河階地的那片光臘樹林裏幾道幽晃的光束。我感覺體內的血液竄逆,毛孔全張!有記憶以來,隱約記得六、七歲時曾目睹過父親深鎖在五花八門的工具間裡的長長獵槍!就那麼一回吧?!即便後來餐桌上偶不時令人一振的出現野味,大約都瞭解那是設置cleclu(陷阱)的功勞。 而後我偶在村子裡或逢十月列管時派出所裡見識過各式各樣的獵槍,令我著迷的往往是那已然泛起油光槍紋肌里。看,終歸看。當槍聲的迴盪在星華鋪潤著的荖濃溪ʹ床上,它其實結結實實撞穿我內心自以為是的浪漫情懷。雖則我依舊迷戀於某種族群原型的片面(斷),但無論山海族群都已叩臨到21世紀的時空場域上。我也企求回歸眾多事物的基本面,然而誰都明瞭簡單不來...。我甚至缺乏勇氣再望去那曾經視狩獵為天賦本能而如今形同繳了械的布農大哥們;即時他們仍有氣質,卻無可避免的因職業而無法那麼的「有為者亦若是」...。 「喔,有人來逛『夜市』囉!」Ibe自麻袋裡鑽出,邊添柴火邊淡淡地說著。我其實真想在後頭補上一句—「手好癢喔!」;然而我終究什麼也沒說不出口。倒是靠在石邊的Haisul慢慢接著:「外面的工作愈來愈沒有了,很多人慢慢的回來,整地、種菜...逛夜市的人也就會比較多了。」這讓我想起有一回在潭南部落與DamaHesul聊天,他說遇在夜裡渡溪的時候,對面山裏好像飛著「螢火蟲」一般,這裏一點,而狗吠不斷的「盛景」,聽的我無限神往。 就像當我獨自在日本領台的時期,日人「理蕃」志業裡留有特殊地位的布農長者—Lahoahla(拉荷阿雷)一家所攸攸生活過23年頭的玉穗故宅遺址間,凝望著原是臥舖與穀倉的位置上已分然成長出三株亭亭大樹;四周的牆垣即使佈滿著落葉與苔蘚卻仍挺守默默護佑之姿,而地板面上已然盡是野芋與山蕨的恣意。即使如此,我仍無限嚮往昔日的炊煙鼎沸!一如鹿野忠雄在一九三一年的夏天登上玉山南峰時所寫下的感懷:「密林中的斑點大概是蕃人的耕地吧。穿過那赭色崩石坡的那一條橫紋大概是蕃人的獵路罷。那麼炊煙冉冉升起的溼谷一角,應該是蕃社的位置罷。這些都是拉荷阿雷和他的黨羽,以及從郡大社奔過去加入抗日行列的郡大蕃,盤踞於這塊大土地,過著原始生活的象徵。」 我眼前隨風飛揚而終於落下的台灣胡桃木片片的野黃落葉彷彿附議、見證...。在有限的文字線索去重建距今八、九十年甚爾百年前的族群面貌,就如同在拼湊著永遠多一片少一塊的拼圖。當然你盡可以反駁我歷史的虛實云云。在20世紀始,初初來台的各項日人的調查裡,而有「台灣蕃界第一人」的森丑之助與晚後但同樣熱血澎湃的鹿野忠雄的文章都深刻記錄著曾經叱吒於東部拉庫拉庫溪流域與盤踞玉山以南的拉荷‧阿雷與阿里曼‧西肯這對兄弟的影響力曾給予他們在深入台灣山林的調查行旅裡所承受的沉重壓力以及某種向慕憧憬。更遑論日人所稱其「全台最後末歸順蕃」以及此間各種解說書籍、牌示裡所指為「抗日英雄」...又或者是數天來引領並扶持我一路走進此境的拉荷同族後輩身上,讀不出Tamaho的風起雲湧之於他們除了對前輩的循例敬意外或可蘊合其他重要的、特別的「意義」;這該是誰的歷史?或說該要有怎樣的「歷史思惟」,或許靜立在家屋後壁的牆垛間一塊迥異於此的花崗岩質材的石碑上印刻著:「布農拉賀阿雷玉穗社遺址 2000‧12‧17立碑 」可以真正發聲吧...。 至於我,倚靠在長於臥舖位置的那棵大樹,閉上眼,靜靜地,彷彿回到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的盛夏,一行日人翻山越嶺來到已然歸順五年的拉荷‧阿雷的居家之所;空氣中漫著樟樹的微香,因為那個時候,Tamaho已有來此指導製樟的二位平地人呢! 一切都在改變哪,如同山腳下未曾稍息的滔滔溪水...。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製作,所有內容均受智慧財產權及相關法律保護。
基本資訊
- 原始資料連結
- 資料來源
- 主題分類
- 建檔單位
- 作品語文中文
- 地圖
本網站使用Cookies收集資料用於量化統計與分析,以進行服務品質之改善。請點選"接受",若未做任何選擇,或將本視窗關閉,本站預設選擇拒絕。進一步Cookies資料之處理,請參閱本站之隱私權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