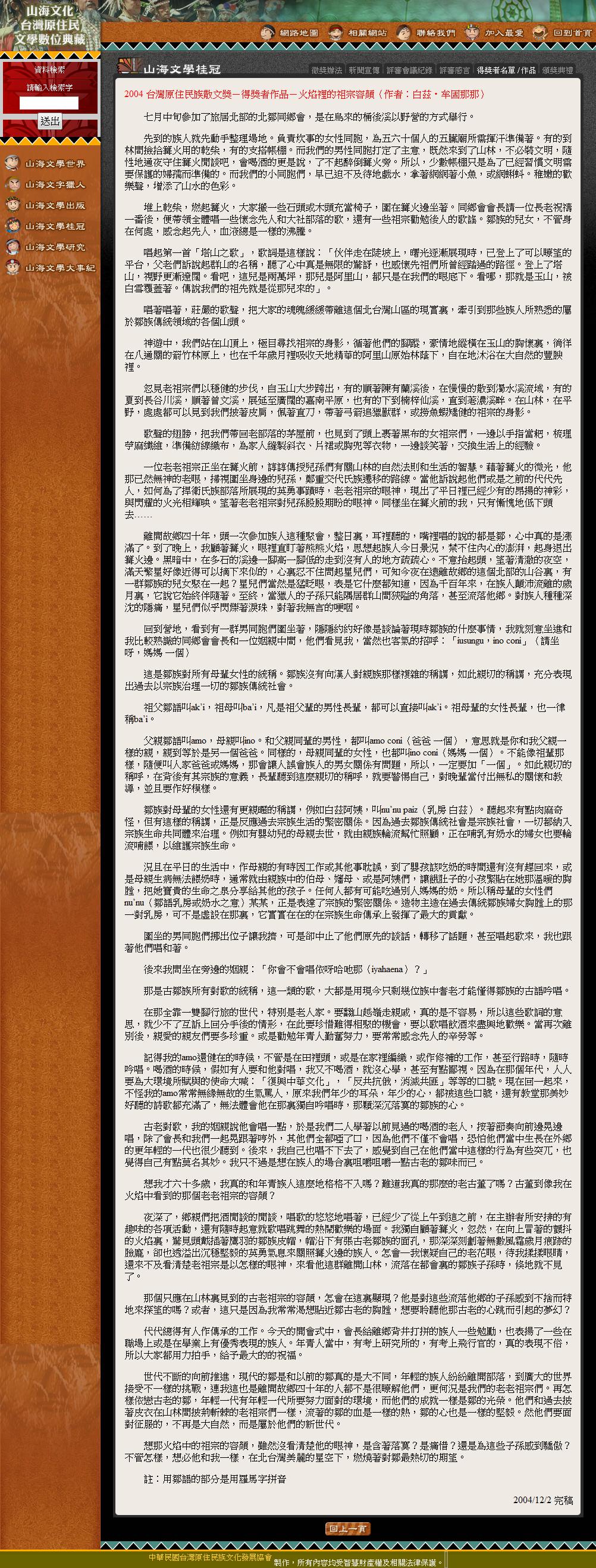跳到主要內容區塊
:::
山海文化 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
山海文化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資料檢索請輸入檢索字2004台灣原住民族散文獎-得獎者作品-火焰裡的祖宗容顏(作者:白茲‧牟固那那) 七月中旬參加了旅居北部的北鄒同鄉會,是在烏來的桶後溪以野營的方式舉行。 先到的族人就先動手整理場地。負責炊事的女性同胞,為五六十個人的五臟廟所需揮汗準備著。有的到林間撿拾篝火用的乾柴,有的支搭帳棚。而我們的男性同胞打定了主意,既然來到了山林,不必裝文明,隨性地通夜守住篝火閒談吧,會喝酒的更是說,了不起醉倒篝火旁。所以,少數帳棚只是為了已經習慣文明需要保護的婦孺而準備的。而我們的小同胞們,早已迫不及待地戲水,拿著網網著小魚,或網蝌蚪。稚嫩的歡樂聲,增添了山水的色彩。 堆上乾柴,燃起篝火,大家搬一些石頭或木頭充當椅子,圍在篝火邊坐著。同鄉會會長請一位長老祝禱一番後,便帶領全體唱一些懷念先人和大社部落的歌,還有一些祖宗勸勉後人的歌謠。鄒族的兒女,不管身在何處,感念起先人,血液總是一樣的沸騰。 唱起第一首「塔山之歌」,歌詞是這樣說:「伙伴走在陡坡上,曙光逐漸展現時,已登上了可以瞭望的平台,父老們訴說起群山的名稱,聽了心中真是無限的驚訝,也感懷先祖們所曾經踏過的路徑。登上了塔山,視野更漸遼闊。看吧,這兒是兩萬坪,那兒是阿里山,都只是在我們的眼底下。看哪,那就是玉山,被白雪覆蓋著。傳說我們的祖先就是從那兒來的」。 唱著唱著,莊嚴的歌聲,把大家的魂魄緩緩帶離這個北台灣山區的現實裏,牽引到那些族人所熟悉的屬於鄒族傳統領域的各個山頭。 神遊中,我們站在山頂上,極目尋找祖宗的身影,循著他們的腳蹤,豪情地縱橫在玉山的胸懷裏,徜徉在八通關的箭竹林原上,也在千年歲月裡吸收天地精華的阿里山原始林蔭下,自在地沐浴在大自然的豐腴裡。 忽見老祖宗們以穩健的步伐,自玉山大步跨出,有的順著陳有蘭溪後,在慢慢的散到濁水溪流域,有的夏到長谷川溪,順著曾文溪,展延至廣闊的嘉南平原,也有的下到楠梓仙溪,直到荖濃溪畔。在山林,在平野,處處都可以見到我們披著皮肩,佩著直刀,帶著弓箭追獵獸群,或撈魚蝦矯健的祖宗的身影。 歌聲的翅膀,把我們帶回老部落的茅屋前,也見到了頭上裹著黑布的女祖宗們,一邊以手指當耙,梳理苧麻纖維,準備紡線織布,為家人縫製斜衣、片裙或胸兜等衣物,一邊談笑著,交換生活上的經驗。 一位老老祖宗正坐在篝火前,諄諄傳授兒孫們有關山林的自然法則和生活的智慧。藉著篝火的微光,他那已然無神的老眼,掃視圍坐身邊的兒孫,鄭重交代氏族遷移的路線。當他訴說起他們或是之前的代代先人,如何為了捍衛氏族部落所展現的英勇事蹟時,老老祖宗的眼神,現出了平日裡已經少有的昂揚的神彩,與閃耀的火光相輝映。望著老老祖宗對兒孫殷殷期盼的眼神。同樣坐在篝火前的我,只有慚愧地低下頭去…… 離開故鄉四十年,頭一次參加族人這種聚會,整日裏,耳裡聽的,嘴裡唱的說的都是鄒,心中真的是漲滿了。到了晚上,我顧著篝火,眼裡直盯著熊熊火焰,思想起族人今日景況,禁不住內心的澎湃,起身退出篝火邊。黑暗中,在多石的溪邊一腳高一腳低的走到沒有人的地方疏疏心。不意抬起頭,望著清澈的夜空,滿天繁星好像近得可以摘下來似的,心裏忍不住問起星兒們,可知今夜在遠離故鄉的這個北部的山谷裏,有一群鄒族的兒女聚在一起?星兒們當然是猛眨眼,表是它什麼都知道,因為千百年來,在族人顛沛流離的歲月裏,它說它始終伴隨著。至終,當獵人的子孫只能隅居群山間狹隘的角落,甚至流落他鄉。對族人種種深沈的隱痛,星兒們似乎閃爍著淚珠,對著我無言的哽咽。 回到營地,看到有一群男同胞們圍坐著,隱隱約約好像是談論著現時鄒族的什麼事情,我就刻意坐進和我比較熟識的同鄉會會長和一位姻親中間,他們看見我,當然也客氣的招呼:「iusungu,inoconi」(請坐呀,媽媽一個) 這是鄒族對所有母輩女性的統稱。鄒族沒有向漢人對親族那樣複雜的稱謂,如此親切的稱謂,充分表現出過去以宗族治理一切的鄒族傳統社會。 祖父鄒語叫ak’i,祖母叫ba’i,凡是祖父輩的男性長輩,都可以直接叫ak’i。祖母輩的女性長輩,也一律稱ba’i。 父親鄒語叫amo,母親叫ino。和父親同輩的男性,都叫amoconi(爸爸一個),意思就是你和我父親一樣的親,親到等於是另一個爸爸。同樣的,母親同輩的女性,也都叫inoconi(媽媽一個)。不能像祖輩那樣,隨便叫人家爸爸或媽媽,那會讓人誤會族人的男女關係有問題,所以,一定要加「一個」。如此親切的稱呼,在背後有其宗族的意義,長輩聽到這麼親切的稱呼,就要警惕自己,對晚輩當付出無私的關懷和教導,並且要作好模樣。 鄒族對母輩的女性還有更親暱的稱謂,例如白茲阿姨,叫nu’nupaiz(乳房白茲)。聽起來有點肉麻奇怪,但有這樣的稱謂,正是反應過去宗族生活的緊密關係。因為過去鄒族傳統社會是宗族社會,一切都納入宗族生命共同體來治理。例如有嬰幼兒的母親去世,就由親族輪流幫忙照顧,正在哺乳有奶水的婦女也要輪流哺餵,以維護宗族生命。 況且在平日的生活中,作母親的有時因工作或其他事耽誤,到了嬰孩該吃奶的時間還有沒有趕回來,或是母親生病無法餵奶時,通常就由親族中的伯母、嬸母、或是阿姨們,讓餓肚子的小孩緊貼在她那溫暖的胸膛,把她寶貴的生命之泉分享給其他的孩子。任何人都有可能吃過別人媽媽的奶。所以稱母輩的女性們nu’nu(鄒語乳房或奶水之意)某某,正是表達了宗族的緊密關係。造物主造在過去傳統鄒族婦女胸膛上的那一對乳房,可不是虛設在那裏,它實實在在的在宗族生命傳承上發揮了最大的貢獻。 圍坐的男同胞們挪出位子讓我擠,可是卻中止了他們原先的談話,轉移了話題,甚至唱起歌來,我也跟著他們唱和著。 後來我問坐在旁邊的姻親:「你會不會唱依呀哈吔那(iyahaena)?」 那是古鄒族所有對歌的統稱,這一類的歌,大都是用現今只剩幾位族中耆老才能懂得鄒族的古語吟唱。 在那全靠一雙腳行旅的世代,特別是老人家。要翻山越嶺走親戚,真的是不容易,所以這些歌詞的意思,就少不了互訴上回分手後的情形,在此要珍惜難得相聚的機會,要以歌唱飲酒來盡興地歡樂。當再次離別後,親愛的親友們要多珍重。或是勸勉年青人勤奮努力,要常常感念先人的辛勞等。 記得我的amo還健在的時候,不管是在田裡頭,或是在家裡編織,或作修補的工作,甚至行路時,隨時吟唱。喝酒的時候,假如有人要和他對唱,我又不喝酒,就沒心學,甚至有點鄙視。因為在那個年代,人人要為大環境所賦與的使命大喊:「復興中華文化」,「反共抗俄,消滅共匪」等等的口號。現在回一起來,不怪我的amo常常無緣無故的生氣罵人,原來我們年少的耳朵,年少的心,都被這些口號,還有教堂那美妙好聽的詩歌都充滿了,無法體會他在那裏獨自吟唱時,那顆深沉落寞的鄒族的心。 古老對歌,我的姻親說他會唱一點,於是我們二人學著以前見過的喝酒的老人,按著節奏向前邊晃邊唱,除了會長和我們一起晃跟著哼外,其他們全都啞了口,因為他們不僅不會唱,恐怕他們當中生長在外鄉的更年輕的一代也很少聽到。後來,我自己也唱不下去了,感覺到自己在他們當中這樣的行為有些突兀,也覺得自己有點莫名其妙。我只不過是想在族人的場合裏咀嚼咀嚼一點古老的鄒味而已。 想我才六十多歲,我真的和年青族人這麼地格格不入嗎?難道我真的那麼的老古董了嗎?古董到像我在火焰中看到的那個老老祖宗的容顏? 夜深了,鄉親們把酒閒談的閒談,唱歌的悠悠地唱著,已經少了從上午到這之前,在主辦者所安排的有趣味的各項活動,還有隨時起意就歌唱跳舞的熱鬧歡樂的場面。我獨自顧著篝火,忽然,在向上冒著的顫抖的火焰裏,驚見頭戴插著鷹羽的鄒族皮帽,帽沿下有張古老鄒族的面孔,那深深刻劃著無數風霜歲月痕跡的臉龐,卻也透溢出沉穩堅毅的英勇氣息來關照篝火邊的族人。怎會—我懷疑自己的老花眼,待我揉揉眼睛,還來不及看清楚老祖宗是以怎樣的眼神,來看他這群離開山林,流落在都會裏的鄒族子孫時,倏地就不見了。 那個只應在山林裏見到的古老祖宗的容顏,怎會在這裏顯現?他是對這些流落他鄉的子孫感到不捨而特地來探望的嗎?或者,這只是因為我常常渴想貼近鄒古老的胸膛,想要聆聽他那古老的心跳而引起的夢幻? 代代總得有人作傳承的工作。今天的開會式中,會長給離鄉背井打拼的族人一些勉勵,也表揚了一些在職場上或是在學業上有優秀表現的族人。年青人當中,有考上研究所的,有考上飛行官的,真的表現不俗,所以大家都用力拍手,給予最大的的祝福。 世代不斷的向前推進,現代的鄒是和以前的鄒真的是大不同,年輕的族人紛紛離開部落,到廣大的世界接受不一樣的挑戰,連我這也是離開故鄉四十年的人都不是很瞭解他們,更何況是我們的老老祖宗們。再怎樣依戀古老的鄒,年輕一代有年輕一代所要努力面對的環境,而他們的成就一樣是鄒的光榮。他們和過去披著皮衣在山林間披荊斬棘的老祖宗們一樣,流著的鄒的血是一樣的熱,鄒的心也是一樣的堅毅。然他們要面對征服的,不再是大自然,而是屬於他們的新世代。 想那火焰中的祖宗的容顏,雖然沒看清楚他的眼神,是含著落寞?是痛惜?還是為這些子孫感到驕傲?不管怎樣,想必他和我一樣,在北台灣美麗的星空下,燃燒著對鄒最熱切的期望。 註:用鄒語的部分是用羅馬字拼音2004/12/2完稿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製作,所有內容均受智慧財產權及相關法律保護。
基本資訊
- 原始資料連結
- 資料來源
- 主題分類
- 建檔單位
- 作品語文中文
- 地圖
本網站使用Cookies收集資料用於量化統計與分析,以進行服務品質之改善。請點選"接受",若未做任何選擇,或將本視窗關閉,本站預設選擇拒絕。進一步Cookies資料之處理,請參閱本站之隱私權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