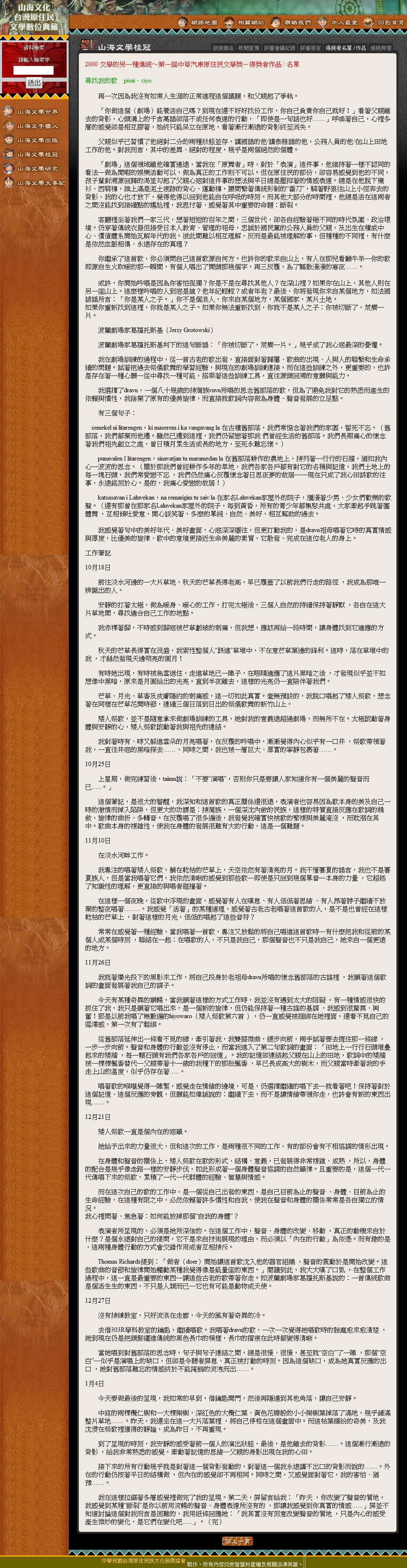跳到主要內容區塊
:::
山海文化 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
山海文化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資料檢索請輸入檢索字2000文學的另一種傳統~第一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得獎者作品/名單尋找我的歌 pisui.ciyo 再一次因為我沒有如常人生涯的正常進程這個議題,和父親起了爭執。 「你做這個(劇場)能養活自己嗎?到現在還不好好找份工作,你自己負責你自己就好!」看著父親離去的背影,心頭湧上的千言萬語卻落不成任何表達的行動,「即使是一句話也好……」呼喚著自己,心裡多層的感覺卻是相互膠著,始終只能呆立在原地,看著漸行漸遠的背影終至消失。 父親似乎已習慣了他絕對二分的兩種狀態並存,講國語的他/講泰雅語的他,公務人員的他/在山上田地工作的他。對我而言,其中的差異、絕對的程度,幾乎是兩個絕然的個體。 「劇場」這個領域離他確實遙遠,當我在「原舞者」時,對於「表演」這件事,他維持著一樣不認同的看法—做為閒暇的娛樂活動可以,做為真正的工作則不可以。但在原住民的部份,卻容易感覺到他的不同,孩子輩對溯源回歸的渴望勾起了父親心底對這件事的想法與平日總是壓抑著的情感表達。總是在他脫下襯衫、西裝褲,換上滿是泥土痕跡的背心、運動褲,腰間繫著傳統形制的“番刀”,騎著野狼往山上小徑奔去的背影,我的心也才放下,覺得他得以回到他能自在呼吸的時刻。而其他大部分的時間裡,他總是活在這兩者之間沒能找到接續點的尷尬裡,我思忖著、感覺著其中重要的命題:斷裂。 客廳裡坐著我們一家三代,想著短短的百年之間,三個世代,卻各自經驗著極不同的時代氛圍、政治環境。仍穿著傳統衣服但接受日本人教育、管理的祖母,忠誠於國民黨的公務人員的父親,及出生在權威中心、價值體系開始瓦解年代的我。彼此間難以相互理解,反而是最能被理解的事,但種種的不同裡,有什麼是依然血脈相傳、永遠存在的真理? 你繼承了這首歌,你必須問自己這首歌源自何方。也許你的歌來自山上,有人在那兒看顧牛羊—你的歌即源自生火取暖的那一瞬間,有個人唱出了開頭那幾個字,再三反覆,為了驅散漫漫的寒夜……。 或許,你開始吟唱是因為你害怕孤獨?你是不是在尋找其他人?在深山裡?如果你在山上,其他人則在另一座山上。這麼樣吟唱的人到底是誰?他年紀輕輕?或者年老?最後,你將發現你來自某個地方,如法國諺語所言:「你是某人之子。」你不是個浪人,你來自某個地方,某個國家,某片土地。如果你重新找到這裡,你就是某人之子。如果你無法重新找到,你就不是某人之子:你被切斷了,荒癠一片。 波蘭劇場家葛羅托斯基(JerzyGrotowski) 波蘭劇場家葛羅托斯基判下的這句斷語:「你被切斷了,荒癠一片。」幾乎成了我心底最深的憂懼。 我在劇場訓練的過程中,從一首古老的歌出發,直接面對著歸屬、歌曲的出現、人與人的聯繫和生命承續的問題。試著把過去祭儀歌舞的學習經驗,與現在的劇場訓練連接,而在這些訓練之外,更重要的,也許是存在著一種心願—從中尋找一種可能,搭乘著這些訓練工具,直往源頭回溯的意願與能力。 我選擇了dravu,一個八十幾歲的排灣族vuvu所唱的思念舊部落的歌,但為了避免我對它的熟悉而產生的依賴與慣性,我捨棄了原有的優美旋律,而直接就歌詞內容做為身體、聲音發展的立足點。 有三個句子: semekelnilitarengen,kimaseremikavangavangla在古樓舊部落,我們常惦念著我們的家園,誓死不忘。(舊部落,我們都棄而他遷。雖然已遷到這裡,我們仍留戀著那我們曾經生活的舊部落。我們長期痛心的懷念著我們祖先創立之處,曾日積月累生活成長的地方,至死永難忘懷。) punavalenIlitarengen,sinavatjantumarumedanla在舊部落耕作的農地上,排列著一行行的石牆,猶如我內心一波波的思念。(關於那我們曾經耕作多年的旱地,我們各家各戶都有對它的名稱與記憶,我們土地上的每一塊石頭,我們常愛戀不忘,我們仍然痛心反覆懷念著日思夜夢的故居——現在只成了我心田詩歌的往事,永遠銘刻於心。是的,我痛心愛戀的故居!) katsasavaniLaluvekan,naremarigimtusaivla在家名Laluvekan家屋外的院子,瀰漫著少男、少女們歡樂的歌聲。(還有那曾在那家名Laluvekan家屋外的院子,每到黃昏,所有的青少年都集聚共處,大家牽起手跳著團體舞,互相傾吐愛意,開心談笑著,多麼的單純、自然、美好,相互幫助的過去。 我感覺著句中的美好年代、美好畫面,心底深深嚮往,但更打動我的,是dravu祖母唱著它時的真實情感與厚度,比優美的旋律、歌中的意境更接近生命美麗的素質,它散發、完成在這位老人的身上。工作筆記10月18日 前往淡水河邊的一大片草地,秋天的芒草長得老高,早已覆蓋了以前我們行走的路徑,我成為那唯一辨識出的人。 安靜的打著太極,做為暖身、暖心的工作,打完太極後,三個人自然的持續保持著靜默,各自在這大片草地間,尋找適合自己工作的地點。 我赤裸著腳,不時感到腳底被芒草劃破的刺痛,但我想,應該再給一段時間,讓身體找到它適應的方式。 秋天的芒草長得實在茂盛,我索性整個人“跌進”草堆中,不在意芒草葉邊的鋒利。這時,落在草堆中的我,才赫然發現天邊明亮的圓月! 有時她出現,有時被烏雲遮住,走進草地已一陣子,在眼睛適應了這片黑暗之後,才發現似乎並不如想像中黑暗,原來是月圓給出的光亮。直到半夜離去,這樣的光亮仍一直陪伴著我們。 芒草、月光、草香及皮膚隱約的刺痛感,這一切如此真實。毫無預設的,我脫口唱起了矮人祭歌,想念著在同樣在芒草花開時節,連續三個日落到日出的祭儀歌舞的新竹山上。 矮人祭歌,並不是隨意拿來做劇場訓練的工具,她對我的意義遠超過劇場,而無所不在。太極啟動著身體與安靜的心,矮人祭歌啟動著我與祖先的連結。 我對著時有、時又躲進雲朵的月亮唱著,在反覆的吟唱中,漸漸覺得內心似乎有一口井,祭歌帶領著我,一直往井底的黑暗探去……,同時之間,我也被一層巨大、厚實的寧靜包裹著……。10月25日 上星期,做完練習後,taimu說:「不要“演唱”,否則你只是要讓人家知道你有一個美麗的聲音而已…..。」 這個筆記,是很大的警醒,我深知和這首歌的真正關係還很遠,表演者也容易因為歌本身的美及自己一時的激情而掉入陷阱,但更大的功課是:排灣族,一個深沈內斂的民族,這樣的特質直接反應在歌詞的精歛,旋律的曲折、多轉音。在反覆唱了很多遍後,我發覺我確實快被歌的繁複與美麗淹沒,而耽溺在其中。歌曲本身的複雜性,使我在身體的發展很難有大的行動,這是一個難題。11月10日 在淡水河畔工作。 我專注的唱著矮人祭歌,躺在乾枯的芒草上,天空依然有著清亮的月。我不懂賽夏的語言,我也不是賽夏族人,但是當我唱著它們,我依然清晰的感覺到那些歌—即使是只回到幾個單音—本身的力量,它超越了知識性的理解,更直接的與唱者碰撞著。 在這樣一個夜晚,從歌中浮現的畫面,感覺著有人在嘆息、有人低低著思緒、有人昂著脖子繼續不放棄的整夜唱著……..。我感覺「活著」的某種道理,感覺著古老古老唱著這首歌的人,是不是也曾經在這樣乾枯的芒草上,對著這樣的月光,低低的唱起了這些音符? 常常在感覺著一種經驗,當我唱著一首歌,專注又放鬆的將自己唱進這首歌時—有什麼把我和從前的某個人或某個時刻,聯結在一起:在唱歌的人,不只是我自己,那個聲音也不只是我自己,她來自一個更遠的地方。11月26日 我就著燭光投下的黑影來工作,將自己投身於老祖母dravu所唱的懷念舊部落的古謠裡,我順著這個歌詞的畫面發展著我自己的調子。 今天有某種奇異的順暢,當我順著這樣的方式工作時,我並沒有遇到太大的阻礙,有一種情感很快的抓住了我,我只是順著它唱出來,是一個新的旋律,但仍能保持著一種古謠的基調,我感到很驚異、興奮!那是以前我唱了無數遍的hiyowaro(矮人祭歌第六首),仍一直感覺被捆綁在她裡面,還看不見自己的遲滯感,第一次有了鬆綁。 從舊部落延伸出一條看不見的線,牽引著我,我雙膝微曲,緩步向前,兩手試著要去握住那一條線,一步一步向前。聲音和身體的行動並沒有停止,而當我進入了第二句歌詞的畫面:「田地上一行行石頭堆疊起來的矮牆,每一顆石頭有我們各家各戶的回憶」。我的記憶卻連結起父親在山上的田地,歌詞中的矮牆被一棵棵楓香替代—父親帶著十一歲的我種下的那批楓香,早已長成高大的樹木,而父親當時牽著我的手走上山的溫度,似乎仍存在著…..。 唱著歌的喉嚨覺得一陣緊,感覺走在情緒的邊境,可是,仍選擇繼續的唱下去—就看著吧!保持著對於這個記憶、這個反應的旁觀,但願能如偉誠說的:繼續下去,而不是讓情緒帶領你走,也許會有新的東西出現……。12月21日 矮人祭歌一直是個內在的底韻。 她給予出來的力量很大,但和這次的工作,是兩種很不同的工作,有的部份會有不相協調的情形出現。 在身體和聲音的關係上,矮人祭歌在歌的形式、結構、意義,已發展得非常複雜、成熟,所以,身體的配合是幾乎像走路一樣的安靜步伐,如此形成著一個身體聲音協調的自然韻律。且重要的是,這個一代一代傳唱下來的祭歌,累積了一代一代群體的經驗、智慧與情感。 而在這次自己的歌的工作中,是一個從自己出發的東西,是自己目前為止的聲音、身體、目前為止的生命經驗,在這種有限之中,必然依賴著許多慣性和自我,使我在聲音和身體的關係常常是各自獨立的情況。我心裡問著、焦急著:如何能放掉那個“自我的身體”? 表演者所呈現的,必須是她所深信的。在這個工作中,聲音、身體的改變、移動,真正的動機來自於什麼?是個永遠對自己的提問,它不是來自技術展現的理由,而必須以「內在的行動」為依憑。而有趣的是,這兩種身體行動的方式會交錯作用或者互相排斥。 ThomasRichards提到:「做者(doer)開始讓這首歌沈入他的器官組織,聲音的震動於是開始改變。這些歌曲的音節和旋律開始觸動某種我覺得像是能量座的東西。」閱讀到此,我大大嘆了口氣,在整個工作過程中,這一直是最重要的東西—讓這些古老的歌帶著你走。如波蘭劇場家葛羅托斯基說的:一首傳統歌曲是個活生生的東西,不只是人類而已—它也有可能是動物或天使。12月27日 沒有排練教室,只好流浪在走廊,今天的風有著奇異的冷。 去借303R學科教室的鑰匙,繼續唱歌。我唱著dravu的歌,一次一次覺得她唱歌時的臉龐愈來愈清楚,她到現在仍是把頭髮纏進傳統的黑色長巾的模樣,長巾的摺痕在此時都變得清晰。 當她唱到對舊部落的思念時,句子與句子連結之間,總是很慢、很慢,甚至就“空白”了一陣,那個“空白”—似乎是演唱上的缺口,但卻是令聽者屏息、真正被打動的時刻。因為這個缺口,成為她真實反應的出口,她對舊部落難忘的情感終於不能掩飾的流洩而出……。1月4日 今天要做最後的呈現,我如常的早到,借鑰匙開門,然後再隱遁到其他角落,讓自己安靜。 中庭的兩棵欖仁樹和一大棵欒樹,深紅色的大欖仁葉、黃色花瓣般的小小欒樹葉掉落了滿地,幾乎鋪滿整片草地……。昨天,我還坐在這一大片落葉裡,將自己停格在這個畫面中。而這枯葉繽紛的奇美,及我沈浸在祭歌裡獲得的靜謐,成為昨日,不再重現。 到了呈現的時刻,我安靜的感受著前一個人的演出狀態,最後,是他離去的背影……。這個漸行漸遠的背影,給我非常熟悉的感覺,牽動著記憶的思緒—父親的身影出現在我的心田。 接下來的所有行動幾乎就是對著這一個背影發動的,對著這一個我永遠講不出口的背影而說的……。外在的行動仍按著平日的結構做,但內在的感覺卻不再相同。同時之間,又感覺面對著它,我的害怕、猶豫……。 我在這樣拉鋸著多層感覺裡做完了我的呈現。第二天,屏留言給我:「昨天,你改變了聲音的質地,我感覺到某種“斷裂”是你以前用流暢的聲音、身體表達所沒有的,那讓我感覺到你真實的情感…...」屏並不知道討論這個對我而言是困難的,我用紙條回應她:「我其實沒有刻意改變聲音的質地,只是內心的感受產生微妙的變化,是它們在變化吧…..」。(完)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製作,所有內容均受智慧財產權及相關法律保護。
基本資訊
- 原始資料連結
- 資料來源
- 主題分類
- 建檔單位
- 作品語文中文
- 地圖
本網站使用Cookies收集資料用於量化統計與分析,以進行服務品質之改善。請點選"接受",若未做任何選擇,或將本視窗關閉,本站預設選擇拒絕。進一步Cookies資料之處理,請參閱本站之隱私權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