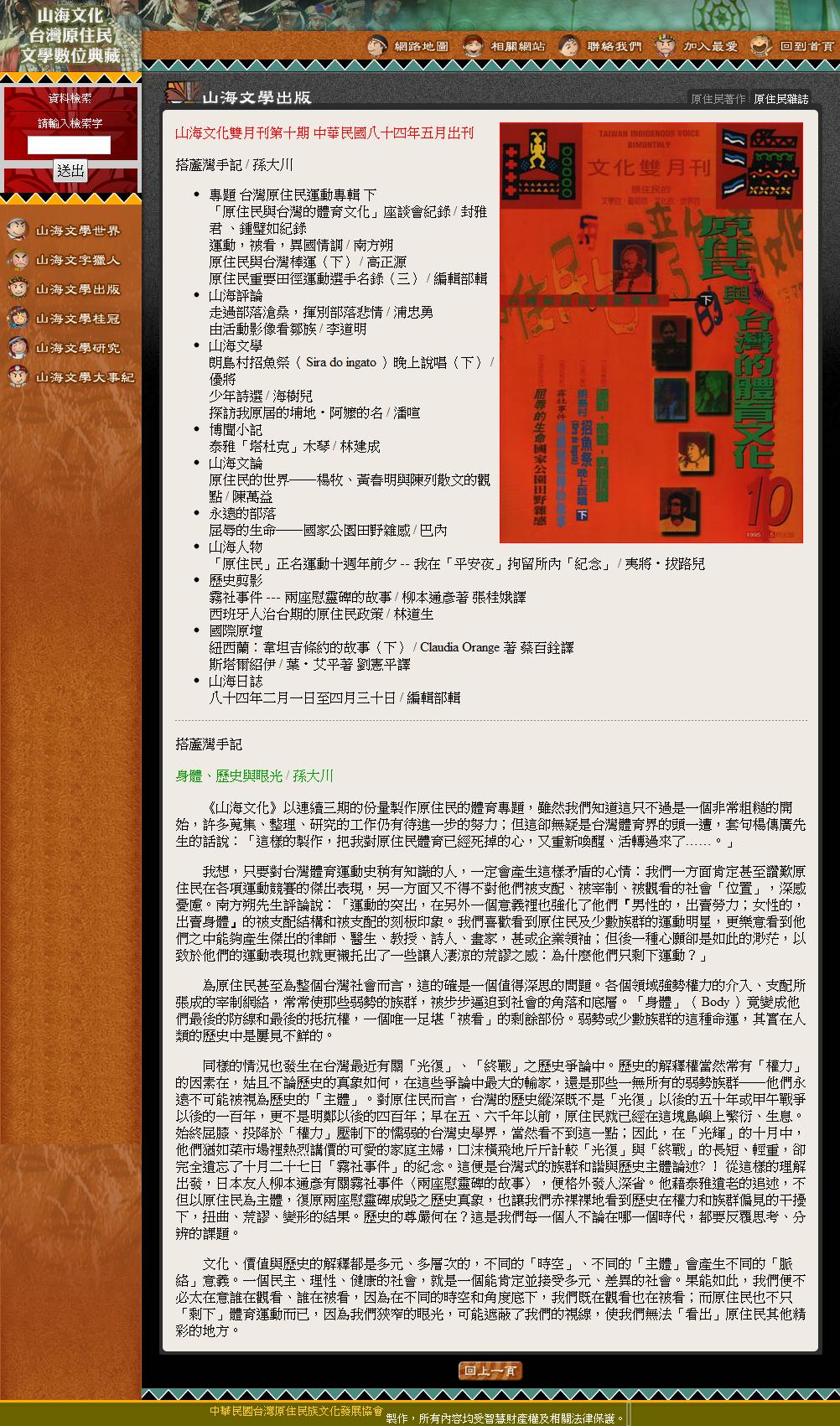跳到主要內容區塊
:::
山海文化 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
山海文化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資料檢索請輸入檢索字山海文化雙月刊第十期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出刊搭蘆灣手記/孫大川專題台灣原住民運動專輯下「原住民與台灣的體育文化」座談會紀錄/封雅君、鍾璧如紀錄運動,被看,異國情調/南方朔原住民與台灣棒運(下)/高正源原住民重要田徑運動選手名錄(三)/編輯部輯山海評論走過部落滄桑,揮別部落悲情/浦忠勇由活動影像看鄒族/李道明山海文學朗島村招魚祭(Siradoingato)晚上說唱(下)/優將少年詩選/海樹兒探訪我原居的埔地‧阿嬤的名/潘喧博聞小記泰雅「塔杜克」木琴/林建成山海文論原住民的世界——楊牧、黃春明與陳列散文的觀點/陳萬益永遠的部落屈辱的生命——國家公園田野雜感/巴內山海人物「原住民」正名運動十週年前夕--我在「平安夜」拘留所內「紀念」/夷將‧拔路兒歷史剪影霧社事件---兩座慰靈碑的故事/柳本通彥著張桂娥譯西班牙人治台期的原住民政策/林道生國際原壇紐西蘭:韋坦吉條約的故事(下)/ClaudiaOrange著蔡百銓譯斯塔爾紹伊/葉‧艾平著劉憲平譯山海日誌八十四年二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編輯部輯搭蘆灣手記身體、歷史與眼光/孫大川 《山海文化》以連續三期的份量製作原住民的體育專題,雖然我們知道這只不過是一個非常粗糙的開始,許多蒐集、整理、研究的工作仍有待進一步的努力;但這卻無疑是台灣體育界的頭一遭,套句楊傳廣先生的話說:「這樣的製作,把我對原住民體育已經死掉的心,又重新喚醒、活轉過來了……。」 我想,只要對台灣體育運動史稍有知識的人,一定會產生這樣矛盾的心情:我們一方面肯定甚至讚歎原住民在各項運動競賽的傑出表現,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對他們被支配、被宰制、被觀看的社會「位置」,深感憂慮。南方朔先生評論說:「運動的突出,在另外一個意義裡也強化了他們『男性的,出賣勞力;女性的,出賣身體』的被支配結構和被支配的刻板印象。我們喜歡看到原住民及少數族群的運動明星,更樂意看到他們之中能夠產生傑出的律師、醫生、教授、詩人、畫家,甚或企業領袖;但後一種心願卻是如此的渺茫,以致於他們的運動表現也就更襯托出了一些讓人淒涼的荒謬之感:為什麼他們只剩下運動?」 為原住民甚至為整個台灣社會而言,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各個領域強勢權力的介入、支配所張成的宰制網絡,常常使那些弱勢的族群,被步步逼迫到社會的角落和底層。「身體」(Body)竟變成他們最後的防線和最後的抵抗權,一個唯一足堪「被看」的剩餘部份。弱勢或少數族群的這種命運,其實在人類的歷史中是屢見不鮮的。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台灣最近有關「光復」、「終戰」之歷史爭論中。歷史的解釋權當然常有「權力」的因素在,姑且不論歷史的真象如何,在這些爭論中最大的輸家,還是那些一無所有的弱勢族群——他們永遠不可能被視為歷史的「主體」。對原住民而言,台灣的歷史縱深既不是「光復」以後的五十年或甲午戰爭以後的一百年,更不是明鄭以後的四百年;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原住民就已經在這塊島嶼上繁衍、生息。始終屈膝、投降於「權力」壓制下的懦弱的台灣史學界,當然看不到這一點;因此,在「光輝」的十月中,他們猶如菜市場裡熱烈講價的可愛的家庭主婦,口沫橫飛地斤斤計較「光復」與「終戰」的長短、輕重,卻完全遺忘了十月二十七日「霧社事件」的紀念。這便是台灣式的族群和諧與歷史主體論述﹖﹗從這樣的理解出發,日本友人柳本通彥有關霧社事件〈兩座慰靈碑的故事〉,便格外發人深省。他藉泰雅遺老的追述,不但以原住民為主體,復原兩座慰靈碑成毀之歷史真象,也讓我們赤裸裸地看到歷史在權力和族群偏見的干擾下,扭曲、荒謬、變形的結果。歷史的尊嚴何在?這是我們每一個人不論在哪一個時代,都要反覆思考、分辨的課題。 文化、價值與歷史的解釋都是多元、多層次的,不同的「時空」、不同的「主體」會產生不同的「脈絡」意義。一個民主、理性、健康的社會,就是一個能肯定並接受多元、差異的社會。果能如此,我們便不必太在意誰在觀看、誰在被看,因為在不同的時空和角度底下,我們既在觀看也在被看;而原住民也不只「剩下」體育運動而已,因為我們狹窄的眼光,可能遮蔽了我們的視線,使我們無法「看出」原住民其他精彩的地方。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製作,所有內容均受智慧財產權及相關法律保護。
基本資訊
- 原始資料連結
- 資料來源
- 主題分類
- 建檔單位
- 作品語文中文
- 地圖
本網站使用Cookies收集資料用於量化統計與分析,以進行服務品質之改善。請點選"接受",若未做任何選擇,或將本視窗關閉,本站預設選擇拒絕。進一步Cookies資料之處理,請參閱本站之隱私權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