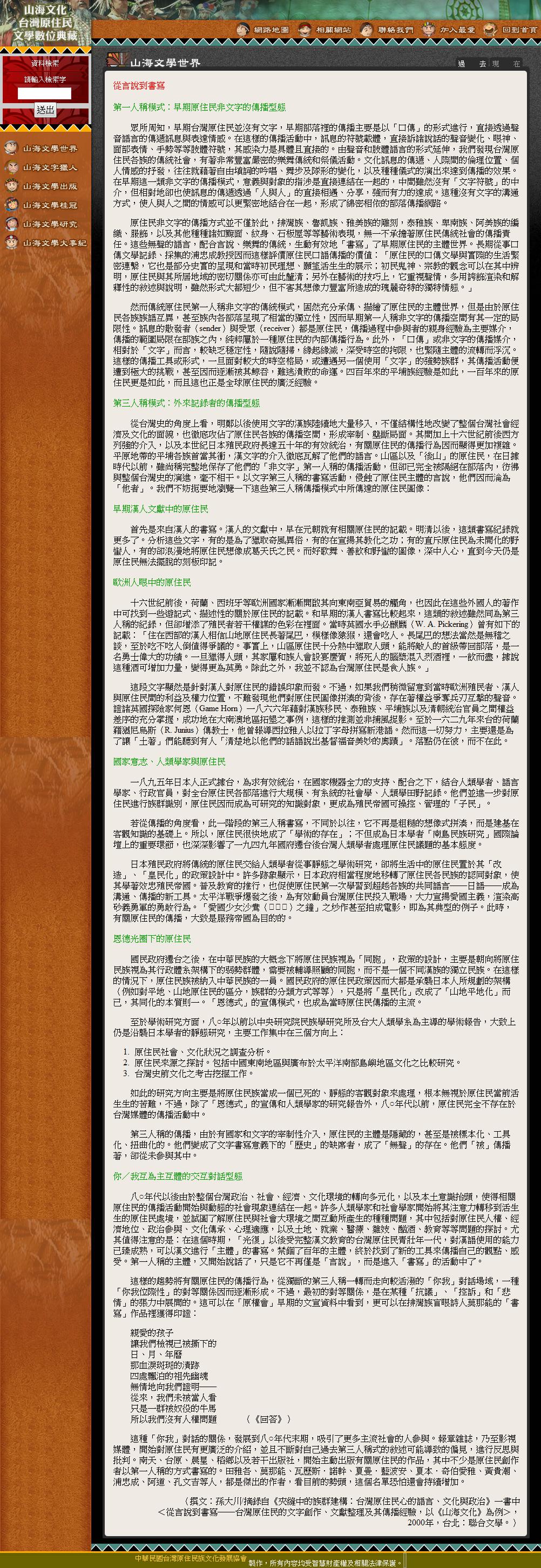跳到主要內容區塊
:::
山海文化 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
山海文化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資料檢索請輸入檢索字從言說到書寫第一人稱模式:早期原住民非文字的傳播型態 眾所周知,早期台灣原住民並沒有文字,早期部落裡的傳播主要是以「口傳」的形式進行,直接透過聲音語言的傳遞訊息與表達情感。在這樣的傳播活動中,訊息的符號載體,直接訴諸說話的聲音變化、眼神、面部表情、手勢等等肢體符號,其感染力是具體且直接的。由聲音和肢體語言的形式延伸,我們發現台灣原住民各族的傳統社會,有著非常豐富嚴密的樂舞傳統和祭儀活動。文化訊息的傳遞、人際間的倫理位置、個人情感的抒發,往往就藉著自由填詞的吟唱、舞步及隊形的變化,以及種種儀式的演出來達到傳播的效果。在早期這一類非文字的傳播模式,意義與對象的指涉是直接連結在一起的,中間雖然沒有「文字符號」的中介,但相對地卻也使訊息的傳遞透過「人與人」的直接相遇、分享,強而有力的達成。這種沒有文字的溝通方式,使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可以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綿密相依的部落傳播網路。 原住民非文字的傳播方式並不僅於此,排灣族、魯凱族、雅美族的雕刻,泰雅族、卑南族、阿美族的編織、服飾,以及其他種種諸如黥面、紋身、石板屋等等藝術表現,無一不承擔著原住民傳統社會的傳播責任。這些無聲的語言,配合言說、樂舞的傳統,生動有效地「書寫」了早期原住民的主體世界。長期從事口傳文學記錄、採集的浦忠成教授因而這樣評價原住民口語傳播的價值:「原住民的口傳文學與實際的生活緊密連繫,它也是部分史實的呈現和當時初民理想、願望活生生的展示;初民鬼神、宗教的觀念可以在其中辨明,原住民與其所居地域的密切關係亦可由此釐清;另外在藝術的技巧上,它重視聲情,多用誇飾渲染和解釋性的敘述與說明,雖然形式大都短少,但不害其想像力豐富所造成的瑰麗奇特的獨特情態。」 然而傳統原住民第一人稱非文字的傳統模式,固然充分承傳、描繪了原住民的主體世界,但是由於原住民各族族語互異,甚至族內各部落呈現了相當的獨立性,因而早期第一人稱非文字的傳播空間有其一定的局限性。訊息的散發者(sender)與受眾(receiver)都是原住民,傳播過程中參與者的親身經驗為主要媒介,傳播的範圍局限在部族之內,純粹屬於一種原住民的內部傳播行為。此外,「口傳」或非文字的傳播媒介,相對於「文字」而言,較缺乏穩定性,隨說隨掃,緣起緣滅,深受時空的拘限,也緊隨主體的流轉而浮沉。這樣的傳播工具或形式,一旦面對較大的時空格局,或遭遇另一個使用「文字」的強勢族群,其傳播活動便遭到極大的挑戰,甚至因而逐漸被其鯨吞,難逃潰敗的命運。四百年來的平埔族經驗是如此,一百年來的原住民更是如此,而且這也正是全球原住民的廣泛經驗。第三人稱模式:外來記錄者的傳播型態 從台灣史的角度上看,明鄭以後使用文字的漢族陸續地大量移入,不僅結構性地改變了整個台灣社會經濟及文化的面貌,也徹底攻佔了原住民各族的傳播空間,形成宰制、壟斷局面。其間加上十六世紀前後西方列強的介入,以及本世紀日本殖民政府長達五十年的有效統治,有關原住民的傳播行為因而顯得更加複雜。平原地帶的平埔各族首當其衝,漢文字的介入徹底瓦解了他們的語言。山區以及「後山」的原住民,在日據時代以前,雖尚稱完整地保存了他們的「非文字」第一人稱的傳播活動,但卻已完全被隔絕在部落內,彷彿與整個台灣史的演進,毫不相干。以文字第三人稱的書寫活動,侵蝕了原住民主體的言說,他們因而淪為「他者」。我們不妨扼要地瀏覽一下這些第三人稱傳播模式中所傳達的原住民圖像:早期漢人文獻中的原住民 首先是來自漢人的書寫。漢人的文獻中,早在元朝就有相關原住民的記載。明清以後,這類書寫紀錄就更多了。分析這些文字,有的是為了獵取奇風異俗,有的在宣揚其教化之功;有的直斥原住民為未開化的野蠻人,有的卻浪漫地將原住民想像成葛天氏之民。而好歌舞、善飲和野蠻的圖像,深中人心,直到今天仍是原住民無法擺脫的刻板印記。歐洲人眼中的原住民 十六世紀前後,荷蘭、西班牙等歐洲國家漸漸開啟其向東南亞貿易的觸角,也因此在這些外國人的著作中可找到一些遊記式、描述性的關於原住民的記載。和早期的漢人書寫比較起來,這類的敘述雖然同為第三人稱的紀錄,但卻增添了殖民者若干權謀的色彩在裡面。當時英國水手必麒麟(W.A.Pickering)曾有如下的記載:「住在西部的漢人相信山地原住民長著尾巴,模樣像猿猴,還會吃人。長尾巴的想法當然是無稽之談,至於吃不吃人倒值得爭議的。事實上,山區原住民十分熱中獵取人頭,能將敵人的首級帶回部落,是一名勇士偉大的功績。一旦獵得人頭,其家屬和族人會設宴慶賀,將死人的腦漿混入烈酒裡,一飲而盡,據說這種酒可增加力量,變得更為英勇。除此之外,我並不認為台灣原住民是食人族。」 這段文字顯然是針對漢人對原住民的錯誤印象而發。不過,如果我們稍微留意到當時歐洲殖民者、漢人與原住民間的利益及權力位置,不難發現他們對原住民圖像拼湊的背後,存在著權益爭奪兵刃互擊的聲音。證諸英國探險家何恩(GameHorn)一八六六年藉對漢族移民、泰雅族、平埔族以及清朝統治官員之間權益差序的充分掌握,成功地在大南澳地區拓墾之事例,這樣的推測並非捕風捉影。至於一六二九年來台的荷蘭籍猶尼烏斯(R.Junius)傳教士,他曾報導西拉雅人以拉丁字母拼寫新港語。然而這一切努力,主要還是為了讓「土著」們能聽到有人「清楚地以他們的話語說出基督福音美妙的奧蹟」。落點仍在彼,而不在此。國家意志、人類學家與原住民 一八九五年日本人正式據台,為求有效統治,在國家機器全力的支持、配合之下,結合人類學者、語言學家、行政官員,對全台原住民各部落進行大規模、有系統的社會學、人類學田野記錄。他們並進一步對原住民進行族群識別,原住民因而成為可研究的知識對象,更成為殖民帝國可操控、管理的「子民」。 若從傳播的角度看,此一階段的第三人稱書寫,不同於以往,它不再是粗糙的想像式拼湊,而是建基在客觀知識的基礎上。所以,原住民很快地成了「學術的存在」;不但成為日本學者「南島民族研究」國際論壇上的重要環節,也深深影響了一九四九年國府遷台後台灣人類學者處理原住民議題的基本態度。 日本殖民政府將傳統的原住民交給人類學者從事靜態之學術研究,卻將生活中的原住民置於其「改造」、「皇民化」的政策設計中。許多跡象顯示,日本政府相當程度地移轉了原住民各民族的認同對象,使其學著效忠殖民帝國。普及教育的推行,也促使原住民第一次學習到超越各族的共同語言——日語——成為溝通、傳播的新工具。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為有效動員台灣原住民投入戰場,大力宣揚愛國主義,渲染高砂義勇軍的勇敢行為。「愛國少女沙鴦()之鐘」之炒作甚至拍成電影,即為其典型的例子。此時,有關原住民的傳播,大致是服務帝國為目的的。恩德光圈下的原住民 國民政府遷台之後,在中華民族的大概念下將原住民族視為「同胞」,政策的設計,主要是朝向將原住民族視為其行政體系架構下的弱勢群體,需要被輔導照顧的同胞,而不是一個不同漢族的獨立民族。在這樣的情況下,原住民族被納入中華民族的一員。國民政府的原住民政策因而大都是承襲日本人所規劃的架構(例如對平地、山地原住民的區分,族群的分類方式等等),只是將「皇民化」改成了「山地平地化」而已,其同化的本質則一。「恩德式」的宣傳模式,也成為當時原住民傳播的主流。 至於學術研究方面,八○年以前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及台大人類學系為主導的學術報告,大致上仍是沿襲日本學者的靜態研究,主要工作集中在三個方向上:原住民社會、文化狀況之調查分析。原住民來源之探討。包括中國東南地區與廣布於太平洋南部島嶼地區文化之比較研究。台灣史前文化之考古挖掘工作。 如此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將原住民族當成一個已死的、靜態的客觀對象來處理,根本無視於原住民當前活生生的苦難,不過,除了「恩德式」的宣傳和人類學家的研究報告外,八○年代以前,原住民完全不存在於台灣媒體的傳播活動中。 第三人稱的傳播,由於有國家和文字的宰制性介入,原住民的主體是隱藏的,甚至是被標本化、工具化、扭曲化的。他們變成了文字書寫意義下的「歷史」的缺席者,成了「無聲」的存在。他們「被」傳播著,卻從未參與其中。你/我互為主互體的交互對話型態 八○年代以後由於整個台灣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的轉向多元化,以及本土意識抬頭,使得相關原住民的傳播活動開始與動態的社會現象連結在一起。許多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開始將其注意力轉移到活生生的原住民處境,並試圖了解原住民與社會大環境之間互動所產生的種種問題,其中包括對原住民人權、經濟地位、政治參與、文化傳承、心理適應,以及土地、就業、醫療、雛妓、酗酒、教育等等問題的探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時期,「光復」以後受完整漢文教育的台灣原住民青壯年一代,對漢語使用的能力已臻成熟,可以漢文進行「主體」的書寫。禁錮了百年的主體,終於找到了新的工具來傳播自己的觀點、感受。第一人稱的主體,又開始說話了,只是它不再僅是「言說」,而是進入「書寫」的活動中了。 這樣的趨勢將有關原住民的傳播行為,從獨斷的第三人稱一轉而走向較活潑的「你我」對話場域,一種「你我位際性」的對等關係因而逐漸形成。不過,最初的對等關係,是在某種「抗議」、「控訴」和「悲情」的張力中展開的。這可以在「原權會」早期的文宣資料中看到,更可以在排灣族盲眼詩人莫那能的「書寫」作品裡獲得印證: 親愛的孩子 讓我們檢視已被撕下的 日、月、年曆 那血淚斑斑的漬跡 四處飄泊的祖先幽魂 無情地向我們證明—— 從來,我們未被當人看 只是一群被奴役的牛馬 所以我們沒有人權問題 (《回答》) 這種「你我」對話的關係,發展到八○年代末期,吸引了更多主流社會的人參與。報章雜誌,乃至影視媒體,開始對原住民有更廣泛的介紹,並且不斷對自己過去第三人稱式的敘述可能導致的偏見,進行反思與批判。南天、台原、晨星、稻鄉以及若干出版社,開始主動出版有關原住民的作品,其中不少是原住民創作者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書寫的。田雅各、莫那能、瓦歷斯.諾幹、夏曼.藍波安、夏本.奇伯愛雅、黃貴潮、浦忠成、阿道、孔文吉等人,都是傑出的作者,看目前的勢頭,這個名單恐怕還會持續增加。(撰文:孫大川/摘錄自《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心的語言、文化與政治》一書中<從言說到書寫——台灣原住民的文字創作、文獻整理及其傳播經驗,以《山海文化》為例>,2000年,台北:聯合文學。)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製作,所有內容均受智慧財產權及相關法律保護。
基本資訊
- 原始資料連結
- 資料來源
- 主題分類
- 建檔單位
- 作品語文中文
- 地圖
本網站使用Cookies收集資料用於量化統計與分析,以進行服務品質之改善。請點選"接受",若未做任何選擇,或將本視窗關閉,本站預設選擇拒絕。進一步Cookies資料之處理,請參閱本站之隱私權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