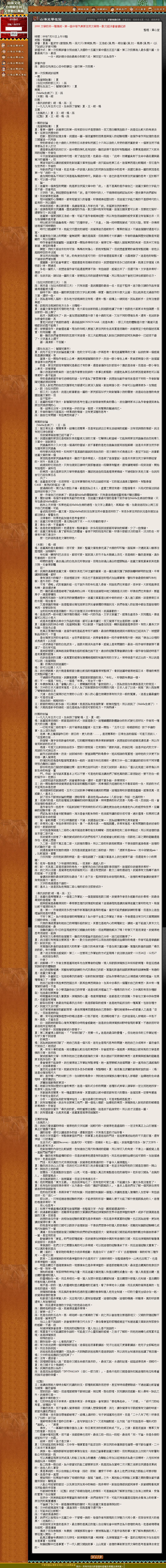跳到主要內容區塊
:::
山海文化 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
山海文化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資料檢索請輸入檢索字2000文學的另一種傳統~第一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散文組決審會議紀錄整理:黃心宜時間:89年7月31日上午10點地點:紫藤廬評審:夏曼‧藍波安(達悟族,男)、孫大川(卑南族,男)、王浩威(漢,男)、胡台麗(漢,女)、楊澤(漢,男)。(以下記錄以字首代稱)評選方式:第一次投票評審分別由進入決選的十五篇文章中選出五至六篇。第二次投票每人最多選六篇,分數最高六分,最低 一分。統計總分後自最高分取前六名,第四至六名為佳作。評審內容孫:請各位先排出心目中的順位,進行第一次投票。第一次投票統計結果一票:〈危崖與險灘〉:夏〈在拉夫郎的那三天〉:孫〈霧社生活之一:智障兒事件〉:夏兩票:〈MaMa生病了〉王、孫〈木屐〉楊、胡四票:〈尋找我的歌〉胡、楊、孫、王〈一九九九年五月七日,生命拐了個彎〉夏、王、胡、楊五票:〈走風的人〉夏、王、胡、楊、孫〈紅點〉夏、王、胡、楊、孫一票的討論〈危崖與險灘〉:夏夏:看第一遍時,我覺得它的第一段有部份似乎是想像的,但又想凸顯某些路子。我是從比較大的角度去看,從原住民歷史的 悲劇、歷史的記憶去看,我選這一篇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與個人的經驗相關。這個作者作所記憶的是我父親輩這一代所接 受的教育或小他十歲的人所受的日本教育和民國三十六年以後的人所受的國民黨教育。一個原住民不曉得要為日本人打仗 還是要為國民政府打仗,這中間的掙扎他有談到,雖然談得不是很好有點籠統,但畢竟是提到了大家共同的經驗。作者在 今天這個資訊發達的時代裡,做了這些反思。他最後一段說,「此時,如釋重負卸下生命中最莊嚴與最寒冷的重擔。」如 果這句話可以讓我感覺到他對這篇文章有些詮釋,我只能給他第三名。這個東西是比較籠統,但它是內在世界的。作者的 年齡我們並不知道,他並未進一步談個人對自己的民族在這歷史中的思考,我選它最後一篇的原因是他第一句「我的一生, 處在兩的極為不同卻又同是極為橫逆的時代」與最後一句,這也許是所有原住民普遍的思考。至於刪不刪,可以進一步討 論。王:這篇有一個典型的問題,就是原住民寫文學中的「我」,是不是真的是作者自己。這篇文章的文字能力很不錯,但會用此 文字的「我」與經歷那些事件的「我」是不同時代的人,不曉得胡老師認為如何。歷史事件我們都知道,但我覺得他寫過 程中細膩的心情轉折,都有相當深入的著墨,好像親身經歷似的,但這個文字能力真的不是那時代的人能有的。所以選的 時候很困惑。像以前李喬、吳錦發等漢人作家也用「我」來寫原住民的東西。孫:這類表現原住民遭遇、歷史過程的作品,散文類中就有好幾篇。這個主題其實可以做,但要把它寫好,還要努力。我沒選 這篇第一個原因跟王浩威一樣,可能不是作者親身經歷。所以有些很細緻的感受其實沒有發揮出來,只在每個轉折處用當 時比較流行的語彙表現,例如「巴嘎呀若」、「天皇」,隔一段時間就變成「反攻大陸」等等,彷彿將這幾個不同時間的 時代口號鋪陳下來,就能交代歷史的過程。我覺得這仍是較取巧、簡單的寫法。不過這個題材還是可以寫。楊:這篇有些文類上的問題。毫無疑問,雖然是揣測,但就像剛才大家講的,作者的語彙與歷史經驗是有距離的,所以在轉折 時作者會抓幾個重點。這篇其實一開始非常吸引我,覺得它有一種詩人描寫東西的角度,但其中又有些套語、典型的場景、 陳腔,例如大哥回來如何可憐、媽媽如何傷心,那就有點隔了。但我想虛實間的拿捏有點困難,若他以超越時空的手法寫 原住民共同經驗,則「我」的角度依然是可行的,但作者還是寫得太實、太露痕跡了。這是他的缺點。不過若我們增加圈 選篇數,我可能會考慮它,裡面還是有很精彩的部份。我想裡面有很多口述的故事,就像王安憶寫《長恨歌》時,問過很 多老一輩的人,我想這個作者可能還是問得不夠,有些細節、感覺出來了,但還不夠。文字是非常好,像詩。胡:在我來說,類似這一篇的文章,若要挑出來的話還有好幾篇,所以現在我不會把它排在前面的名次。〈在拉夫郎的那三天〉:孫孫:再來是〈在拉夫郎的那三天〉,只有我選,是我圈選的最後一名,但並不堅持。這次散文類的作品有個通病是鑿痕太露, 餘味不夠。選這一篇的原因是它的文字比較流暢、樸實,雖然沒有什麼大企圖,但比起其他太過造作的文章,還好一些。王:因為是年輕人寫的,很多地方該裁掉的沒有裁,還有一點,結構上一線到底。因為是新手,沒有注意節奏感。楊:該裁而沒裁掉的地方太多,太囉唆。夏:這篇文章有個很可惜的地方是,他大哥在回家的路上到底跟他講了什麼?他跟他大哥原本有些隔閡,但回家的一路上聊了 起來,隔閡消失了。我一直在想這隔閡是什麼?差十歲的兄弟,又在不同的環境生長。還有,他回家參加教會的活動,其 實他只敘述了表面的過程,最後能說BUNNUNSAK(我是布農),那三天他的體驗是什麼?難道只是唱歌到欲罷不能嗎?胡:若要選佳作,我會選這篇。現在的年輕人要進入原住民的生活其實是很難的,我覺得至少他的描述很真實,如何接觸、感 動,雖然我們會想得到的怎麼只有這樣,但三天能開始進入對自己族群的認同及興趣中,已經很不錯了。文字基本上還不 錯,滿清新、不俗膩。〈霧社生活之一:智障兒事件〉夏:我先不從文字去討論這篇文章,他的文字可以進一步再思考。看完這篇簡單的文章,給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讓我構圖,有 圖像。從一開始作者搭上公車,遇見兩個智障的孩子,然後一群小學生上車,欺負那兩個小孩。這個圖像值得令我們思考 的是,原住民部落有智障兒是最近才有的事,還是普遍存在於部落中?應該是後者。但是這一群小學生上車來,卻覺得智 障小孩是該被欺負的,這也是作者要去批評的。故事比較鬆散,我選他為第五名的原因是覺得他可以寫得更好。最不能接 受的是最前面作者引述峨格的話,似乎是為了要累積字數,我想這在創作者而言是很不好的。作者對智障兒應該得到同情、 陌生人對他們的自然反應等地方都還可以更深入描寫,對這兩個小孩,作者可以詮釋得更多。在情感上,跟〈在拉夫郎的 那三天〉比起來,我是比較喜歡這一篇的。原民部落似乎欠缺對智障小孩的關懷,我是站在這樣的角度選這篇文章的,但 並不堅持。王:這篇的格局不夠大,對智障兒的思考也僅止於對弱者被欺負的關心,我在讀時原本以為作者會提到身為原住民被歧視的心 情,結果也沒有。沒有更進一步的反省、聯想,只有簡單的難過而已。夏:作者的確也只是寫出一時單純的情緒,沒有更深層的思考。孫:語言也有問題。有些東西用錯了。兩票的討論〈MaMa生病了〉:王、孫王:寫日常生活,簡簡單單,結構也很簡單,但是有記錄出日常生活細瑣的感動,沒有很誇張的情節。我沒有把它排在前面, 但我覺得寫這樣已經不錯了。孫:我選這篇的原因也是相對於其他鑿痕太深的文章,它顯得比較溫暖。它能夠將原住民語彙很自然地帶入文章中,這對原住 民語彙將來介入中文是一個滿好的嘗試。我不喜歡的是他在語彙後面用括弧解釋,這是未來原住民作家在運用原住民語彙 時所要共同思考的。如何將不是漢語的語詞用很自然的、很文學的方式表達出來,甚至不加註。我喜歡這篇文章的第一個 原因就是將原民語彙帶進來,雖然不是非常感人,但是做了這個嘗試。這是未來原住民文學所要經營的。另外,就像王浩 威提到的它很自然,只有在提到日據時代莫那魯道這一段顯得有鑿痕,還有講媳婦那一段到後面,開始有說理的、資料性 的東西,這也是原住民文學所要處理的,應該把這些段落處理得更精細。不過相對於其他文章,在我而言它已經在第五名 內了。楊:這篇是很可愛,也很特別,從沒有事情的地方找出細節來寫。它的寫法滿像王醫師的。有點像個CASE、案例式的寫法。前 面滿精彩的,姨丈為什麼肚子痛,都是因為日本人,虛實之間很有趣。但整個看來,片段式的寫法到結尾時卻好像少了什 麼,作者自己也缺席了,跟這個MaMa的關聯較弱,只有最後透過祖靈祝禱才顯出關聯。夏:關於結構,每個作者都有其創作的用意,但這篇文章最可惜的是看不到作者在MaMa生病後的情緒,只有在最後MaMa邀他一 起向上天祈禱。如果他能在MaMa生病的過程,在文字上嚴肅化、再真誠一點、在最後這段加上兩三百字自己的感觸,可能 會成就很好的一篇文章。因為MaMa的狀況在原住民中算是很好的了,有很多原住民的狀況是你連加油都沒辦法、看醫生也 沒得看的,如果他能加進來思考會更好。孫:這篇文好像很悠閒,像太陽光照下來,一片片移動的樣子。夏:像生小病,不是重病。楊:這是他故意壓抑的。他還是有一點掉書袋,許多段落到後面都用學術的解釋,少了一些情緒。胡:這篇文章每個人看了都有自己的體會,會被不同的段落所打動。好像什麼都淡淡的進來,淡淡的走,好像有什麼又像沒什 麼。也許這就是他文筆的特色。〈木屐〉:楊、胡楊:這篇真的是生動精彩,很可愛、清新,整篇文章就像充滿了木屐的叩叩聲。描寫第一次遇到漢人嚇得往屋裡跑、油桐樹叫 布杜樹、鞭炮叫巴古吉古,都很可愛。寫到漢人砍竹子為木屐錦上添花,很是精彩。雖然是懷舊,滿多愁善感的,但亦有 時間的進程,過去滿山的白色浪花好像回音,但現在卻滿山滿谷的塑膠製品。這篇文章就算拿到其他散文獎,也會得到矚 目。胡:我真的滿喜歡這篇文章,相較於其他刀斧沈重的篇章,這一篇生動反應了族群接觸時鮮明的記憶。平常講族群接觸,都好 像有頂很大的帽子,但這裡面沒有,而且也不是套固定的程式在詮釋事情,譬如作者最愛的樹叫布杜樹,是外來的,作者 不用「侵略」式的意識形態,也不說外來的布杜是入侵者,而說他們也有需求、很辛苦。大家相處得很和樂,最後還送東 西。雖然最後還是破壞了她最美的山林,可是在這過程中她父親總是淡淡的,好像我們也有需求,要蓋房子,總是要犧牲 些東西來換取。在原住民的變遷過程中,這篇文章算是比較中肯的敘述。漢人進入鄒族,卻是要做日本的木屐,現在看來 又是懷舊的情緒。這是整個台灣包括原住民社會變遷的複雜狀況,我們每個人的記憶中都含混著這樣的東西,若要採取完 全的批判角度是很難的。所以它這樣淡淡中帶有批判,我滿喜歡的。楊:這是我們一般中國文學抒情的傳統。年輕一代的作品,文字太華麗了,感情生產很多,反而尷尬。像這篇可以用以小見大 或是其他讚美古典中文作品的用語,都可以拿來講它,但又覺得不完全是那麼一回事。夏:這篇在我的排名中跟〈危崖與險灘〉可以對調,不論是在段落、轉折處都處理得很好。有的人賣弄文字知識,但這未必是 他真正累積的知識,這個作者則是能思考而不鋪張。最後的問題是她提到木屐現在已經消失了,被塑膠製品所取代,不僅 是台灣原住民的社會如此,全世界都是如此。我常會看最後一段作者要表現什麼,她說「懷念山谷裡的成長歲月,以及那 一波波綿延不斷的白色波浪。」這跟木屐消失這件事,感覺上是有問題的。最後一段作者好像變得不嚴謹了,但也有可能 是她對塑膠工業興起後對環境生態的感傷也說不定。過去的經驗累積會讓我在看一個作者在描述時是不是有真實的感情, 也許這是我的主觀。這真實的感情在建構她理解的知識所用的文字上,有時候是不成正比的。所以我是可以把〈危崖與險 灘〉的票改投到這篇的。楊:你可以拉票!大川孫:我也想跑票。我大概是看前面分數比較低的幾篇看得有點煩了,看到這篇時覺得她寫日本、環境的東西也有點斧鑿之痕。 不過聽你們這麼說,我願意跑票。裡面提到鄒語的漢人「布杜」,好像跟布農話一樣。胡:不,一個是「布杜」,一個是「布得」,完全不一樣。夏:布農族稱漢人是「會騙人的人」,更嘲諷的則是「會放屁的人」,因為放屁在布農族是很大的禁忌。楊:文中的日本大道很有意思,日本人為了控制鄒族各村而開的大路,日本人走了以後,她寫「族人就捨棄了彎彎曲曲的日本 大道,走自己覺得抄近方便的小山徑,族人的心靈也被釋放得有如天空一般的寬廣」,這是全篇最重的話,可是很恰當, 很自然的,剛剛好的。王:前面的兩段比較多餘,可以刪掉。就是因為有這個敗筆,較無完整性,所以我挑了〈MaMa生病了〉。楊:大概就是新手的緣故,這也是她為什麼很可愛的地方。不夠熟練。四票的討論〈一九九九年五月七日,生命拐了個彎楊、王、夏、胡〉楊:這篇寫得很精彩,前面是詩的形式,後面是散文。這種韻體跟散體融合的形式變化很好玩。作者用一種很大的主觀,壓倒 一切地來寫二哥的意外。我不覺得這是鑿痕。從文章一開始,「五月七日/母親節將近/放下手邊的事,坐上漆灰色的 老車/車上瀰漫著昨日的、前日的、更久的酒/……」是很簡單的,日常生活的描寫,可是又很詩人,「從望鄉出發…/ 拐個彎,揮手告別教會的牧師」它的觀照視覺效果非常新鮮強悍,我想這部份的感嘆很濃很濃,所以作者用新詩的形式來 表達,可是又比新詩自由很多,想到什麼就寫,也有類似「國家共匪」的詞出現,這是手記式的文字,用詩的方式排出來, 創作出詩的節奏。然後,回到城市的、要直接戰鬥的場景中,短兵相接的現實裡,這時他的文字更不加修飾,讓人覺得他 的憤怒和悲傷是和整個現實連在一起的,這個方向也很精彩。還有文中一些二哥講話的部份用不同字體特別凸顯把口語的 部份和他自己描述的距離拉開,這效果也挺好玩的。然後又回到詩,最後以「僅以此見證二哥受傷以來對生命的執著、奮 鬥」作結,這句話其實基本上可以不要,可是他的寫法讓我們了解他真的跟二哥很貼近,要不然在一般的寫作中,他要以 上述那段話來說服我們,我會覺得多餘。還好,他還不算多餘,非常特別。王:我一開始看的時候覺得詩是用哥哥的觀點來寫的,用車禍那天經過的地方來看哥哥的一生,用詩的方式來呈現生命是怎麼 被消磨掉的悲劇過程,五月七日回到車子轉彎後遇到的問題,這種屈辱和折磨還是繼續。感情很真,很感動人,基本上, 談了很多不斷被討論的問題,酒啦等等,最後他用pasibutbut(八部合音)作結,也滿好的。夏:很湊巧的是,他的這種寫法和蘭嶼的純粹傳說故事、拜拜慶典的形式很像。先唱一段,然後說一段,會用這樣的表達形式, 是作者在作一些思考,可能新詩較不受拘束的形式可以讓他更自由地去表達他內心的感受和世界。從蘭嶼的經驗來看,我 們認為海洋是會支配情緒的,海洋是會支配食物的。他後面所講的部份很可惜,過於濫情,如果將它濃縮到哥哥生命的描 寫,會較具體,又可以呼應前面。不過,我還是給它第一,因為結構特殊也具有創意。胡:非常用心寫,有些非常好的佳句,像「一具具米酒,一瓶瓶屍體」非常有意思。較有問題的是敘述者的部份。前面詩的部 份可說是模擬進入二哥的心境來寫這故事的發生和轉彎,因他覺得他和二哥非常貼近,所以用這樣的語言來替二哥代言, 但我覺得太詩意了。雖然變成詩的形式我們格格不入的感覺會比較削淡些,但跟他二哥之間的距離還是存在,感覺上想進 入二哥,但那不真正是二哥。太詩意的關係,所以二哥的形象就較間接,不像後面的直接表達。這樣的形式雖然不錯,但 我還是覺得有刻意的痕跡。反而是後面直接引述二哥的話,例如:「酒原來是davus,如今卻變成pais。」比較直接,衝擊 力反而強。然而他對酒的辨證,是一個老話題了。這篇文章基本上我也覺得不錯,但還是有小小的問題。楊:他有一點像是「少年維特的煩惱」,很清新,滿感人的。胡:對,尤其是二哥是很衝突的角色,一直要洗白自己的這個影像很強烈,這個部份我覺得非常好。孫:我之所以沒選,是覺得他就用詩寫就可以,還沒有想到詩、散文二者的連結性。我覺得有文氣轉不過來的感覺,不太習慣, 會讓我放棄的最後原因則在最後「來!走下去,堅持探索生命旅程的勇氣」,這樣的東西會讓我覺得不夠有說服力。當然, 文字的表達還是不錯的。胡:基本上,這是因為他模擬二哥心境的部份沒那麼成功。〈尋找我的歌胡、楊、孫、王〉王:這篇也是兩種筆法,一個是工作筆記,一個是描寫他跟父親。我覺得作者很多感動來自於尋根,到最後尋到的是理智,情 感與感覺是最難得到的。尋根要怎樣找到情感和感覺?這個過程就是讓我覺得這篇文章好的地方。幾個比較不理想的地方 是,第一,作者提到很多西方劇作家葛羅托斯基等的理論,當然可能受戲劇訓練的影響,但是加上這些理論到底是好還是 不好?第二,為什麼是這樣的兩種筆法?為什麼不全是工作筆記?再者,作者還是沒有交代文章開頭與父親的爭執;父親 代表的傳統價值和她自己的兩種形態的對立,其實也是她內心的兩種對立,讓她一直不能進入原來文化的情感跟感覺,最 後雖然講出1月4日的呈現感受到父親離去的背影,但這問題就解決了嗎?好像又不是很清楚。我覺得她思考很細密,能夠 思考到文化尋根的這個層次,雖然夾用理論來協助自己分析,這已經很難得了。夏:我沒選它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散文在敘述時可以用自我的理解去詮釋你的表達,作者可能是學戲劇的,對我來說,引 用葛羅托斯基的話是個很大的敗筆。從散文的角度來講,不是在做文獻回顧,葛羅托斯基的話跟「尋找我的歌」有什麼關 連?我沒有辦法感覺到。第二,一定要用工作筆記的方式呈現嗎?我沒辦法接受。11月26日、12月27日……她到底在尋找 什麼?胡:我解釋一下。作者主要是運用她早先在原舞者的經驗,矮人祭歌跟排灣族五年祭祭歌兩種,希望從透過別族的歌的體驗跟 自己的經驗相遇,用藝術學院訓練的方式找尋自己的歌。葛羅托斯基的話跟原舞者的訓練無關。有趣的是,這篇文章多重 斷裂、多重對立,包括她尋找的過程。在新的制度裡面,認為你要尋找自己必須透過大師的理論,在某種情境之下,想要 把自己記憶中某些東西挖掘出來,跟某些東西做接合,在其中去尋找一個屬於自己的東西。其中有一種質變的過程,不是 原來的樣貌,多少要混融你自己的特質,這是在歐洲理論之下一種尋找的方式。文中真的有很多種斷裂,包括最初原舞者 時期團員如何進入賽夏族、排灣族的心靈,表達某種情感,這都是很大的困難。作者在文章中拼命想尋找,但都是有某種 斷裂在那裡。她最後所能尋找出來的,就是那斷裂的感情。這是她所能抓住的一種真實。包括各種方式,到處交叉去行歌、 在芒草堆被痛苦的劃割等等,最後某種東西還是她自己想像的,譬如她覺得dravu的歌動人之處是「空白」,但這是她的詮 釋;有可能排灣族理想中的唱法是要一口氣不斷地、很流暢地唱下去,也許這個老人家唱到一半氣不夠,換氣,才產生空 白,這跟她的斷裂心境有某種契合時就會感動她。這是我在做排灣族田野時發現的事實。不過我很好奇最後她所呈現的是 什麼樣子,到底聲音變成什麼樣子。夏:第二頁重複上面的說,「『你被切斷了,荒癠一片』這是我最深的憂懼。」但在她後來的工作筆記裡,似乎又看不到這樣 的東西。楊:因為她說她被切斷了,她自己就是一個片段,這完全是現代思考的問題。她把自己分成兩半,當然會找不到自己。她很認 真,煞有介事的感傷,她在體會比較古老的東西時,你會感受到一個差異。席勒說以前荷馬的文學是素樸的文學,後來就 變成感傷的文學,如果你把自己定義成感傷的文學,就永遠回不到素樸的東西。這素樸與感傷的距離是原本就存在的。夏 曼會覺得不能接受,我也覺得這工作筆記有點滑稽,她一直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卻一直用自己滿感傷的方式,去追尋素樸, 當然完全追尋不到。就變成有很多很多的解釋,有點囉唆。夏:她很專注波蘭的劇場家說的話,(楊:這是台灣後現代大 師)是作哪一門的田野工作,在田野的場景中,例如她在排灣族古樓村看老人家唱歌、詮釋她的生命過程時,感受應該比 波蘭這個劇場家更深。楊:她都沒有探討歷史社會的東西。這是一個形式分析的問題,這種形式美學人類學家一定立刻把她拆穿。就像有人說為什麼 京劇道具很簡單,有一種虛實的美學,其實這跟以前中國很窮有很大的關係,這個因素一定要考慮進去。作者完全是形式 分析,一直認為祭歌有種神祕性,一直在追尋它的神祕性,可是有點胡思亂想。夏:我有這種感覺。我去年去屏東三地門,聽一個老人唱歌、詮釋他的東西,排灣族老人對他的歌的解釋是非常美的。作者並 未把這部份當作「尋找我的歌」時的重要出發點,這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我才沒選這一篇。孫:我有選這篇,比起其他篇,這篇算是寫得很細膩的。五票的討論〈走風的人〉孫:我自己看這篇的時候,覺得他的文字挺順、挺輕巧的。我覺得他是虛擬的,一定沒有真正上山打過獵,真正打獵應不像他 講的這樣,還可以講這麼多的話,還看到雲豹,只有傻瓜雲豹才給你看。楊:他的文字很靈巧,有點像唐望的門徒,而事實上他是爸爸的門徒,爸爸要傳述給他的不只是打獵,還有神話、口述傳說、 生活方式。講到Discovery,這滿巧妙、可愛的,很精彩。和上一篇比,我發現靈巧很多,除了文字外,他是比較有方法, 他對這樣的內容也比較誠懇,他知道自己現代和傳統的距離,所以有切入的角度,不像上一篇感覺上是一直敲門敲門都不 應。雖然他有點虛構的部份,但是我覺得他還是有的說服性,而且他這樣的詮釋也挺可愛的。在這個過程中,他是爸爸的 門徒,用天真的方式來得到知識,我覺得他做得滿好的,不會令人覺得尷尬。夏:雖然我沒去山上打獵,但我也可以非常深入地去看這篇文章。他並沒有說明他的父親是怎樣的,與山神、與自然土地的親 密關係,只是焦點放在雲豹、山羌,可是一個獵人真正的焦點是在他的過程中。他形容父親為「走風的人」,是跟著風走, 走在風前面的人,這麼厲害,但並沒有表達出來。楊:他的問題是「東方主義」,把自我神祕化了,但有他的可愛之處,不能講太多,講太多就沒意思了。夏:他有些形容詞用得非常好,比方最後一段的「應該叫跟風的人」,基本上是我們在了解一個民族在使用語言的時候絕對有 他的自然背景,長期孕育下來的知識,而這樣的知識對一個獵人來講就是獵人建構的人生哲學。有些話很好,如「低ㄈㄧˊ 那立按」,只有經過這樣經驗的民族,才能使用的形容。蘭嶼人便不太能了解什麼是跟風走的人。這樣的表達非常好,有 用心在思考。王:如果不考慮虛構或真實性這個問題,他整個文字、內容、觀察都還滿好的。胡:我滿喜歡這篇的。很難得有這樣的文章讓我們接近排灣族的世界中這麼神聖的境界。或許不該猜測這是誰的文章,但若是 我想的這位作者,我相信這經驗的真實性是非常高的,而且是非常真實的經驗。也正因為這樣,更加地讓我覺得珍貴。真 的就是有這樣的父親可以跟孩子這樣對話,不像我們想像中的獵人那麼傳統,很難把知識跟經驗轉化成現代知識和下一輩 溝通。但在這裡面這個父親顯然和我們的認知差距很大,覺得這個父親很能將這樣的觀念和語言教導下一輩,甚至用的言 辭會讓你有「唐望」的門徒那種感覺,但我覺得在排灣族中真的有這樣的父親,而且在排灣族的智慧傳承這部份,我是非 常佩服的,他們父子之間關係真的可以非常親,可以把這樣的經驗傳承下來,而且這個經驗太寶貴了,可以真的看到里古 飉(雲豹),看到牠的場景也令我非常感動,就是在ㄖㄚˊ古樹下。ㄖㄚˊ古是種欒樹,樹的籽有二種作用,一是可以做 肥皂,二是排灣族的祭司最神聖的珠子也是用ㄖㄚˊ古樹籽做的。在整個過程中,山羌也出現了,也是非常神聖的,這說 明里古飉也不是隨便捕食的,牠要捕食也是非常神聖的,都是那麼難得出現。最後里古飉真的就像百步蛇一樣,牠有一種 預知的感覺,有股特殊的神祕力量。而且這篇文章把獵人和里古飉完成疊在一起,獵人就是里古飉,里古飉的靈魂和獵人 的靈魂貼在一起,而且長相也一樣,獵人在想什麼里古飉都知道,里古飉想什麼獵人也知道,里古飉的呼息和獵人的呼息 幾乎是一致的,獵人的靈魂和里古飉靈魂的互通性,看了非常地令人感動,而且我真的覺得是真的,包括他的語言,用的 排灣族的辭彙,而且風的意像和迅速的里古飉的意像和獵人他完全知道,一切的力量完全結合在一起,我覺得這樣的意像 和象徵力是非常驚人的,況且現代的人還有這樣誠實、這樣的經驗、這樣的機遇,好難得,真的好訝異還有人有這樣的經 驗,而且還有這樣的文字能力把他結合起來。孫:聽胡老師這麼一說,就覺得這篇非常棒。王:變第一名了。孫:他是在我的五名內,張、胡老師一說才漸漸的了解,我之所以會這樣主要是跟祖父、父親的狩獵經驗不是這樣,通常他門 在山上是不說話的,我會覺得好像交代太多了,像在看唐望的那種感覺並不知道這篇文章對我有那麼多的感動,不過,我 知道排灣族會這樣,但就我的經驗而言,獵人在山上是不說話的。胡:現實是不太可能講那麼多話的,可能是父子心靈契通的感覺,之後才了解的。而他把她轉化成現實來呈現,這是排灣族很 特殊的部份。孫:聽你這麼一說,心意就改變了。胡:有次我去訪問一個排灣族的爸爸,這個爸爸很喜歡講話,兒子比爸爸又更喜歡講話,他兒子全部幫他回答,而且告訴我說, 我爸爸就是這樣講的,因為我一天到晚跟我爸爸聊天是這麼說的,所以我完全知道我爸爸講了幾百遍。楊:文中的爸爸應該已經死掉了。胡:沒有,還活著。楊:因裡頭那個老人說「那是你父親生命歲月換來的」,最後又說,永遠的記憶,結尾結得很美,很輕巧。夏:他父親才五十幾歲吧。楊:我真的這麼以為的。孫:這是因為這裡說的「DIVINALIAN(低ㄈ一那力按)」,是表示他的父親是個快如風這樣的地位和尊重而換來這樣的榮耀。〈紅點〉王:這讓我想起大學時去幫忙抗議的狀況,那種剝削真的很悲慘,甚至有時候還要賠錢。不過這篇比較著重在親情,雖然會聯 想到控訴、憤怒,但這裡面親情不斷被拉鋸、被拉開、懸在那裡,反而讓我很感動,耐人尋味。除此之外,我覺得它是一 篇很平常的散文。楊:它的特色是句子非常長,感情非常深、非常直接,會有類似「要老媽老命」、「天哪」、「殺千刀的哈馬星」這種詞。句 子雖然很長,但不會讓人覺得堆砌,反而讓人想慢慢咀嚼、消化,讓你覺得句子跟感情有交錯的味道。前面先講他們居住 的環境,後來居住環境都破壞了,結構上滿好的;句子穿插運用也很好,但是「二十八年了吧!好像很久了似的,卻又記 憶鮮明得彷彿才是昨日的事。」這句穿插太多了。又很有幽默感,比方說「這不如說是另一種形式的『搶親』」、「黑得 像炭」、「一幕幕的苦難依舊在上演,和日漸荒涼的故鄉互映成『灰』」之類,都是很直接、簡單又有力的意象,而且在 悲痛中嘻笑怒罵,很不錯,後面節奏也很好,最後三段一段比一段短,最後用「而,不論,你是多麼的絕望和不甘,也罷」 結束,很好。這才是文學。夏:它的結尾很乾淨俐落,文中有一種事實是不能否定的,原住民的命運像惡性循環一樣不斷在重複,二十八年來不單單是阿 美族,每一個族群都有這樣的事情在發生,我自己蠻喜歡這篇文章的,但如果說能加上四到六句家屬和船公司的對話,就 可以具體呈現原住民或漢人的船工在海上的遭遇,凸顯船公司在以經濟追求為最大目標時,人性如何被操縱玩弄。年輕的 船工就像一張白紙,為什麼當初找船工都要原住民,就是因為在當時二次大戰之後原住民還是很單純的,這些人的人事背 景是單純的,所以在被船公司知會、招收、限制、遭受不平時,基本上他們沒有能力跟船公司要求賠償,這是作者一直想 要說明的。如果說作者除了母親的哭訴、描寫「搶親」之外,真把船公司與船工家屬之間的關係當作議題來探討,顯現漢 人船公司經營的面目,以及原住民在其中的無助,就非常好。對這些情節我感同身受,我曾親眼看見原住民船員的手因意 外斷掉的情景。〈紅點〉敘述了母親在陸地上的情形,可是誰能夠了解原住民船工在海上被欺負、受傷的實情?在台灣原 住民中,阿美族能寫非常豐富的海的故事,我們這幾年下來,可能只有這篇是從陸地去看海上的故事。原住民的真實遭遇, 不論過了多少年,都是應被開發的題材。所以這篇文章是值得探討的。楊:文中的感慨滿有力量、滿滄涼的,但就是層次還不夠。王:可能年紀比較輕。孫:不過抓得滿準的。夏:我們可以發現在十五篇之中,不管哪一族的,每個作者所展現的文字魅力大同小異,但背後有很大的差異。〈走風的人〉 中到底有沒有雲豹是其次,最主要的是真正的獵人在台灣社會中被界定為什麼樣的角色,他是破壞環境生態呢,還是遵循 傳統?但在泰雅族、布農族、排灣族等社會中,要被稱為獵人不是件容易的事。要了解布農族的男人,要從獵人開始,才 能真正體會布農族的文化特性。對排灣族來講,南排灣、北排灣獵區不一樣,雲豹出現的地方在生態而言是事實,在排灣 知識經驗中也是事實。下一代人聽父親說故事、上山見習,這樣的事對原住民文學的思考是值得去肯定的。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製作,所有內容均受智慧財產權及相關法律保護。
基本資訊
- 原始資料連結
- 資料來源
- 主題分類
- 建檔單位
- 作品語文中文
- 地圖
本網站使用Cookies收集資料用於量化統計與分析,以進行服務品質之改善。請點選"接受",若未做任何選擇,或將本視窗關閉,本站預設選擇拒絕。進一步Cookies資料之處理,請參閱本站之隱私權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