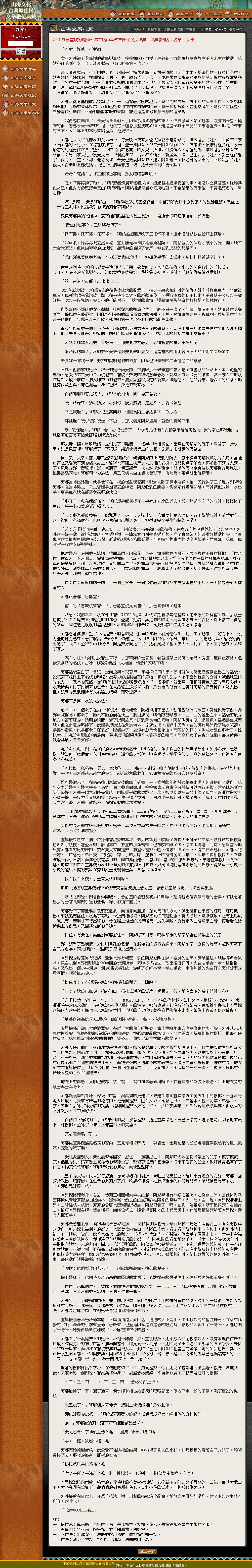跳到主要內容區塊
:::
山海文化 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
山海文化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資料檢索請輸入檢索字2001來自靈魂的觸動~第二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得獎者作品/名單-女巫 「不對,疑慮,不對勁!」 女巫阿鄔卸下背蔞裡的龍葵與臭椿,搖搖頭喃喃自語。左顴骨下方的臉頰皮肉與右手沒來由的抽動,讓她心裡感到不安,今天清晨醒來,這已經是第三次了。 每天清晨醒來,不下雨的天氣,阿鄔一定揹起背簍,到村子邊的河床上走走,採些作物、野菜什麼的。她與幾個老姊妹淘,在那裡蓋了個小工寮,取名「天天來」,並經常在這裡煮野菜與地瓜切塊的稀飯當早餐吃。七旬的一群老婦,平日最喜歡這樣的清晨休閒了。但今天起床後,阿鄔就感覺不對勁,心悸、臉皮抽動,連手掌也莫明奇妙的抖動。她以為身體出了什麼狀況,但接連三次後,她感覺應該有什麼是要發生。「有事發生嗎?好事發生?壞事發生?大事發生?小事發生?」 阿鄔又從背蔞裡取出幾顆大小不一,還黏著泥巴的地瓜,習慣性的自語。幾十年的女巫工作,因為祝禱詞與慣用咒語的音律要求,阿鄔已經習慣在自言自語的時候,將一句話分斷,並重複尾句,她多半時候並不自覺這個小動作,不過朗誦詩歌般的音調,讓她還是喜歡有意無意的這麼說。 「我得趕快動作了,今天很多事勒。」阿鄔扒清背蔞裡的東西,伸展腰背,站了起來。沒有滿天星,健康的很。想起今天一堆的行程,她決定不理會那些皮跳心悸。走進屋子時不自覺的向東邊望去,那是台東市的方向,太平洋上的雲彩有點怪異,她覺得。 阿鄔是大八六九部落的女巫頭子,每天晚上總有人登門拜訪或電話預約「搭拉芼」(註)。由留守在家照顧阿鄔的三兒子,在臨睡前排定行程,並告知阿鄔。第二天阿鄔例行的休閒回來後,便按行程實施。今天排定的行程比往常多了些。村子口古山家念高三的女兒,成績好但沒信心,希望阿鄔「搭拉芼」給她開智、給信心;馬山家大兒子後天入伍,求個護身符;古麥家不信邪,新居落成沒「巴里西」(註),就已經住進了一個月,一直不平靜,最近反悔,今天也要請阿鄔來。還好阿鄔刪掉了新進見習女巫的「卜拉法」(註)儀式,否則加上應允給村長兒子生病驅邪這一樁,她今天可真的要忙翻了。 「母母!電話!」才正要跨進客廳,孫女嚷嚷著叫喚。 「喔,不要再排了勒。」阿鄔想起清晨有個老姊妹,提起替她媳婦安胎的事,她沒敢立刻答應,推給其他女巫,但對方仍堅持希望由阿鄔安胎。阿鄔接起電話心裡滴咕著,不希望是他們來催。卻突然莫名的一陣心悸...... 「喂...是啊......我是阿鄔啦!」阿鄔突然改成國語說話,電話那頭響起十分誇張大的說話聲調,連坐在一旁的三媳婦,也被吸引的轉過頭看著阿鄔。 只見阿鄔接過電話後,丟下話筒跌坐在沙發上發獃,一堆淚水從眼眶像瀑布一般溢出。 「發生什麼事?」三媳婦嚇壞了。 「怪不得,怪不得,怪不得。」阿鄔搖搖頭連唸了三個怪不得。淚水沿著皺紋在臉頰上擴散。 「叫車吧,妳弟弟老五出車禍,軍方通知準備送往台東醫院。」阿鄔努力的把剛才聽來的說一遍,她不太會說國語,但這回濃濃的山地腔,卻清楚的表達了意思,她感到虛弱的想躺下。 「我也別急著這麼哀傷,全力護著他回來吧。」她揮起手掌抹去淚水,強打起精神站了起來。 候車的同時,阿鄔已經著手準備近三十顆,夾著紅丹、切開的檳榔,小心的放進背起的「拉法」(註)。呼吸的紊亂與心跳,讓她焚香並唸完第一段迎靈祝禱詞,並排下三顆檳榔時險些暈倒。 「玆,古浪尹母那登母哇哇暗......」 唸起祝禱詞後,阿鄔謹慎的在最後離地的腳掌下,擺了一顆夾著紅丹的檳榔。關上計程車車門,坐進後車座。像剛才聽完電話後,跌坐在平時接見客人的舒軟座位上,幾近癱瘓的爬不起來。手裡隨手又扣起一顆紅丹,唸起一段咒語。聲音小的不能再小,但凝重的表情,還是讓司機好奇的頻頻從照後鏡偷瞄。 作為這個小部落的女巫頭頭,這樣緊急的叫車出門,已經不只一次了,但這回情況不同。她清楚的感覺到自己恍惚的有些嚴重,因此特別仔細的準備所需要的法器、工具,謹慎選擇咒語、祝禱詞,並反覆的檢查每一個動作、步驟有沒有作錯。就像她第一次出外勤時的慌亂與緊張。 很多年以前的一個下午時分,阿鄔才結束法力與程序的研習,回家途中被一對像是夫妻的平地人迎面攔下。那對夫妻表情著急與無助,讓她意識到有事情發生,但接下來的對話才讓她吃驚不已。 「阿桑!請妳對阮去台東好唔?」那夫妻注視著她,表情誠懇的讓人不好拒絕。 「啥米代誌勒?」阿鄔雖然覺得這對夫妻舉動唐突,還是禮貌的用她苦練很久的山地閩南語發問。 夫妻妳一句我一句,努力的說明他們的來意,阿鄔也很辛苦的才弄懂他們的意思。 原來,他們家的兒子,唯一的兒子兩天前,在鹿野那一條筆直的讓人忘了有盡頭的公路上,發生嚴重的車禍,急救到第二天中午仍沒醒來,醫院不樂觀的準備放棄急救,請家人作好必要的準備。當一家人在加護病房外哭成一堆時,病人卻奇蹟的醒來。病人氣虛卻清楚的說有人搖醒他,叫他到台東西邊靠山的村落,那裡有個歐巴桑,膚色黝黑,身材短胖,找她來就有救了。 「你們哪耶知道是我?」阿鄔不敢相信,國台語夾著說。 「阮一路走來,納看納找,看到妳,阮丟感覺一定是妳。」說得誠懇。 「不是我啦!」阿鄔心裡是高興的,但因為陌生讓她多了一分戒心。 「拜託啦!阮求您對阮走一下啦!」那夫妻見阿鄔遲疑,著急的要跪下來。 「別...這樣啦,」阿鄔一看,心裡也急了,「你們去把他的衣服帶來看看再說啦...我的家在那邊啦。」她指著前面有著橘色面牆的磚造房說。 那夫妻一聽,沒敢耽誤,立刻搭了車離開,一個半小時後折回,出現在阿鄔家的院子,還帶了一盒水果,說是見面禮。阿鄔想了一下程序,接過他們手上的衣服,施起法術後讓他們帶回。 第二天一大早,那夫妻又出現在阿鄔家,懇請阿鄔隨他們到醫院去。原來經過阿鄔施過法的衣服,當晚覆蓋在又昏迷不醒的病人身上。醫院也不阻止病患家人最後的安慰。沒想到過了午夜,那重傷不醒的人醒來了,巡房的護士發現時,還一直醒著,儀器顯示,病人越來越穩定。所以他們決定直接找阿鄔到病房施法。徵得醫院同意,阿鄔頃全力施法,第三天病人自加護病房移至一班病房,兩週後出院療養。 阿鄔當時出外勤,就是像現在一樣的慌亂與緊張。那家人除了專車接送,第一天就包了三千塊的酬禮給阿鄔,在當時男工一天工資還是四百五的時候,阿鄔收到的酬勞,震驚鄰近幾個部落。而神蹟似的第一次出手,更是奠定她在部落女巫群的地位。 「那孩子,現在還好嗎?」阿鄔想起那個從死神手裡爬回來的男人。又突然驚覺自己的分神,輕輕搖下車窗,將手上扣著的紅丹彈了出去。 「啐!那泥哪瓜蒂絲!」她咒罵了一聲。今天遠比第一次重要且意義深遠,容不得她分神。雖然對自己的巫術道行充滿信心,但這次發生在自己兒子身上,她很難完全平撫情緒的波動。 「茲!八嘎拉染古倆,德母安,...」阿鄔換了一顆夾紅丹的檳榔,在嘴唇上輕沾過以後,祭起咒語。阿鄔的一舉一動,從照後鏡落入司機眼裡,一陣寒意自司機背脊升起,向全身蔓延。阿鄔嘴唇掀動無聲,森冷專注的表情與司機的張惶恐懼,形成強烈與恐怖的感覺。而同時計程車內的溫度也似乎突然急降,讓車行像滑溜一般的安靜與快速。 抵達醫院,陪同的三媳婦,拉開車門。阿鄔俯下身子,慎重的在落腳前,放下握在手裡的檳榔,「拉米拉,依母阿,卜阿啷...」嘴裡唸著祝禱詞下了車。自她學巫術以來,從沒有像現在一樣的謹慎與認真。計程車司機早嚇傻了魂,沒等收錢,直接開車走了。救護車急鳴著,剛好也到達醫院。幾個醫護人員慌張的推出擔架檯車,隨救護車下來的幾個軍人,也立刻將救護車上已經綁緊固定的傷患,抬上檯車,往急診室奔去,見著阿鄔,都點了頭打招呼。 「快!快!前面請讓一讓!」一個士官長,一面慌張著表情指揮推擔架車檯的士兵,一面驅趕著前面擋道的人。 阿鄔跟著進了急診室。 「醫生呢?怎麼沒有醫生?」急診室沒見到醫生,那士官長吼了起來。 「別急,我們看看,現在外科醫生都在手術房,我們立刻聯絡其他醫院固定支援的外科醫生來。」護士也慌了,看看擔架上到處是血的傷患,登記了姓名,與進來的時間,剪開傷患身上的衣物,掛上點滴。傷患的嘴角、胸腔還是漞漞的溢出些血。看的阿鄔一陣暈眩,兩腿軟疲的使她倒退向牆邊。 阿鄔忍著傷痛,望了一眼擔架上躺著的兒子壯碩的身軀,看見他似乎掙扎的坐了起來。一驚之下,一股力量把她托起來,急忙取出一顆檳榔,彈起紅丹後,啐!阿ㄖ依,依母那米吶......」的唸起咒語,連續的低聲唸了一長串,並將手中的檳榔,向擔架方向拋了去,她看見兒子躺了回去,掙扎了一下,坐了起來,又躺了回去。 「喂!小姐,妳們快找醫生來呀!」那帶頭的士官長,看著擔架上受傷的弟兄,胸腔一度停止波動,然後又劇烈的起伏,古嚕...的嘴角湧出一大堆血,情急的又吼了吼。 阿鄔腦袋空白了一會兒,走向擔架。夾著另一顆檳榔紅丹的手,顫抖著伸向傷患已經停止出血的腦袋、臉頰與不規律上下起伏的胸腔。她努力的控制自己的思緒,專心的施法,她不容許絲毫的分神,減低她巫術的威力。一連串的咒語,從阿鄔刻意壓低的嘴唇傾洩。每一個停頓,就出現一個頂著黃色光圈的黑服影像,走近擔架,拊了拊躺著的傷患。在支援醫生還沒來以前,急診室內所有人注視著阿鄔的怪異動作,沒人出聲,詭異的氣氛讓所有人起雞皮疙瘩,頸背涼颼。 阿鄔不是第一次這樣施法。 前些年,一個女子在知本橋附近一個大轉彎,騎機車滑了出去,整個腦袋摔向地面,脊椎也受了傷。救護車趕到時,那女子一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上,胸口起伏,嘴角隨著呼氣,一口一口的推出血來。腦袋著地的地方,留著紅的、透明的液體,流了近兩公尺。送到急診室的同時,阿鄔也應家屬之邀抵達,雖然醫生趕開她,但在家屬的堅持下,她還是想辦法在急診室外,施起法術。接連十天內,在加護病房外做了幾次祝禱。是醫科發達,也是那女子運氣好,腦殼破了,卻沒有顱內大量瘀血。而阿鄔的鎮守,也成功阻止那女子,恍惚中走入急診室與加護病房內,隨時出現的隧道般凡人看不見的暗門。而今那女子在台北謀職,每回休假,總會特地來看看阿鄔。 急診室出現暗門,在阿鄔的分神中逐漸擴大,逼近擔架,傷患胸口的起伏幾乎停止。阿鄔心頭一陣驚慌,她知道事態嚴重。立刻集中精神,謹慎的又祭起一連串咒語,她從沒如此認真的選擇咒語,也從沒有這麼全心施法。 「巴拉擠,烏茹禡,嘎嚥,里地谷,......」每一個間斷,暗門便縮小一點,擔架上的傷患,呼吸就越明顯、平順。而阿鄔越來越大的聲音,越來越急的動作,卻讓急診室的所有人頭皮發麻。 外科醫師來了,在傷患進到急診室後的四十分鐘,一個支援的年輕醫師總算來啦。阿鄔停止了動作,讓出空間給醫生。醫生檢查了傷勢,做了些表面處理,搖搖頭表示台東沒有醫院可以施行手術,建議轉院到西部比較好。阿鄔一聽立刻感覺暈眩,兩腳幾乎軟的要跪了下來。卻見到急診室又出現了暗門,逐漸的變大。心頭一驚,一股力量又把她撐了起來。伸手進「拉法」,再取出一顆紅丹,拋了去,「啐!」的輕輕咒罵,暗門縮了些,阿鄔不敢怠慢,嘴裡無聲的唸起咒語。 「......他媽的爛醫院,沒設備......需要轉院,......直昇機?什麼?......直昇機?...是...是...,謝謝隊長。」帶隊的士官長,透過手機與單位聯繫。斷續又口不擇言的回答聲音,毫不保留的傳達焦急。 受傷的是阿鄔在空軍服役的五兒子,單位早在車禍第一時間,向空軍總部回報,總部指示海鷗的S70C,必要時出勤支援。 直昇機果然在半個小時抵達醫院旁的草坪,強大的氣漩,吹斷了幾棵大王椰子的莖葉,幾棵芒果樹枝幹也斷裂了幾枝。甚至阿鄔下計程車時,放置的那顆檳榔,也被吹的離了位,滾向水溝邊。此時,急診室內那只有阿鄔看的見的暗門,突然變大欺向擔架,將整個擔架吞噬。傷患抽慉了一下,胸口停止起伏。阿鄔大吃一驚,「拉惡死,烏日夫,衣昵諺,啐!」的大喊,並將手上的檳榔拋向那暗門,那暗門像相機快門,立刻縮成一個小原點。而傷患被電擊似的,胸口激烈起伏,忽...喝...忽...喝的激烈呼吸聲,穿過直昇機巨大的聲響,把擠在門口看直昇機降落的一群人的注意力吸引回來。只見血塊隨著傷患急促的呼吸,從嘴角一小塊一小塊的溢出,慌的緊靠在旁的護士及幾個士兵,拿著紗布擦拭。 「快!快!上機。」士官大聲的叫喊。 啪啪...強烈的直昇機旋轉翼聲音夾著氣流湧進急診室,讓急診室顯得更加的慌亂與緊張。 「別站在門邊,門會自動開啟。」急診室的護理長費力的叫喊,想提醒幾個靠像門邊的士兵,卻被急著出去的士官長開門引進的聲浪「嘩」的頂了回去。 阿鄔受不了那聲浪以及緊張氣氛,向後靠向牆邊,並向門口的方向,彈出緊扣在手裡的紅丹。紅丹拋出,卻被風門擋住,吹偏了落點,卡進門槽縫裡。阿鄔望向紅丹落點處,黃光泛起,逐漸擴散,在門上形成一道光門。而剛才不時出現的,像在牆上熔出的灰黑暗門卻消失無蹤,急診室內白牆還是白牆。再看看急診擔架上的傷患,又回復先前的平穩。 「挺住,有我在,無論如何要挺住。」阿鄔呼了口氣,眼神堅定的望了望躺在擔架上的兒子。 護士調整了點滴瓶、針口與鼻孔的氣管,並將填妥的資料表送來。阿鄔花了一分鐘的時間,顫抖著簽下自己的名字,同意轉診。交回原子筆後走出門外。 直昇機的旋翼沒有減緩,聲浪也沒有轉弱,震的阿鄔心跳加速,窒息的感覺,讓她暈眩。她無暇理會這些,逕自走到直昇機與急診室中間的水泥道旁,同時從「拉法」取出檳榔紅丹,夾在右手食、中、姆指指尖。又取出一個小牛銅鈴,銅鈴頂端穿孔處,穿綁了小紅布塊,她左手食、中指熟練的夾在紅布與銅鈴間的環洞柄,順勢搖起鈴來。 「挺住呀!」心裡浮起急診室內掙扎的兒子,一陣酸。 「啐!」她停止搖鈴,抬起袖口,橫抹去湧起的淚水。咒罵了一聲,她沒太多的時間精神分心。 「八嘎拉然,蒙日奈,瞪母暗......」她吸了口氣,全神貫注的搖起鈴,祭起咒語,銅鈴聲,念咒聲,與漸漸誇張的儀式動作,吸引急診室附近所有人的注視。那份詭異,卻沒分散擔架旁,急著推出傷患上直昇機的幾個人的張惶。擔架一出急診室大門,推送的士兵吆喝著往直昇機快步走去,帶隊士官長不停的催促。 「早些送往高雄八0二醫院,應該還有機會。」每個人都這麼想。 直昇機穩定卻巨大的旋翼聲,帶隊士官的催促吼叫聲,護士提醒推車人注意傷患的尖叫聲,阿鄔越來越急的搖鈴聲,咒語祝禱詞悠遠深邃的嗡唈聲,在強勁紛亂的氣流下,交迭紛沓。持續斷折的樹枝,揚飛不停的灰塵,讓急診室到停機坪短短的十幾公尺,像極了戰場撤離前的景況。 阿鄔沒停止動作,眼睛注視著擔架移動。卻發覺幾縷淡淡的黑霧從周遭滲出,而且自擔架離開急診室大門時便開始。她還注意到,黑霧逐漸凝結成團,顏色也愈來愈濃,從灰白轉灰黑,以擔架為中心移動、集結。不一會兒,濃黑的霧開始旋轉,逐漸逼向擔架。從阿鄔眼裡望去,一個巨大的灰黑色隧道形成,像黑色的龍捲風即將吞噬整個擔架所有人,而擔架旁的人逃難似的推著擔架,快速向直昇機移動。糟糕的是,擔架前方靠直昇機位置,此時也形成了一個小隧道暗門,而且逐漸擴大。兩個暗門一前一後,活像有生命似的不停擴大並聯手要吞噬擔架。 擔架上的傷患,又劇烈鼓起,咳了幾下,幾口血含著碎塊噴出,在直昇機的氣流下飛送,沾上擔架旁的護士與士兵身上。 阿鄔額頭開始冒汗,深吸了口氣,銅鈴搖的更起勁。揚起手來向直昇機方向拋去手中的檳榔,一團黃光隨即形成,化去前方暗黑的隧道門。她走向擔架,隨手又取了兩顆紅丹,「烏魯木,嘎一泥案,烏魯木,茲,啐啦!」唸了唸分解的咒語,隨即向擔架後方拋了去。巨大的灰黑暗門立刻分解成幾縷黑霧,但頑固的不肯散去,在四周遊移。 「你們鬥不過我的!」阿鄔自信的說,扶著擔架,送進直昇機裡,自己上機前,還不忘記在腳離地前放下一棵檳榔,並唸了一句阻止邪靈跟上的咒語。 「艾咕哇而浪...啐...」 阿鄔從直昇機搖晃起飛的窗內,望見停機坪四周,一群護士、士兵倉皇的紛紛走避直昇機起飛的巨大氣流,感激的流了淚。 「我能救回別人,我也能帶你回家,挺住,一定要挺住!」阿鄔眼光收回到擔架上的兒子,摸了摸額頭,低聲的說。跟著登上直昇機的帶隊士官,整理著傷患的固定帶,從來不信邪的臉上,也好像突然瞭解了什麼,抬頭望望阿鄔。阿鄔感激他的用心,向他點點頭。 九點多的太陽,說來還算舒適,從直昇機窗口射進,直貼上傷患臉上,看起來有幾分的安詳。阿鄔收回銅鈴取出一顆檳榔,在傷患的肩頭拊了拊,唸起祝禱詞,在狀況穩定的這段時間裡,她想搶點時間多唸一些,讓傷患舒服一些。 直昇機持續爬升,右旋,機頭正朝西轉向中央山脈,阿鄔覺得有些噁心暈機,左側窗口外,景像從海平面轉換成青綠蒼鬱的山脈森林,還沒完全散去的山嵐薄霧在陽光的照映下,光一塊,白一塊。直昇機漸漸上昇,山稜線越來越近,薄薄的雲層也逐漸貼近機身,阿鄔只看了一眼,感到一陣暈噁,隨即撇過頭向右邊窗口,恰巧直昇機右轉,機身傾斜,由座位望去,還看得見剛才的士兵與護士,遮著眼睛抬頭望著直昇機,還有人揮著手。 阿鄔暈著闔上眼,嘴裡持續唸著祝禱詞。一個影像閃進腦海,她突然睜開眼擠向右邊窗口,唐突與慌張的動作,引起機上幾個人的好奇,也跟著擠向窗口。帶隊的士官,看了看覺得無趣坐回座位上。但阿鄔臉上卻一下子轉成青綠色,她看見擔架上的兒子,正從人群中離開,向醫院左側太平間慢慢走去,而太平間旁幾個著卑南族傳統黑衣,頭頂淡黃色透明光環的老婦,正目不轉睛的看著她兒子。而其中一個老婦唸唸有詞,手指指向她兒子來的方向,開出一條泛黃影的路。阿鄔認出那是她活了一百多歲才過世的曾祖母,也是夢裡引領她進入巫師行列,並在每天臨睡前的寤寐中,不斷傳她法力的師父。阿鄔沒來得及趕上他曾祖母在世,但傳授法力的過程,她已經見過無數次,她再熟悉不過了。那老婦拋起紅丹,抬起頭微笑的朝阿鄔望了一眼,每個動作緩慢卻穩定精準。 「糟糕!他們要收回老五了!」阿鄔驚叫著靠回擔架的兒子。 機上醫護兵,也同時發現傷患的血壓變的非常低,心跳微弱的幾乎停止,連呼吸也好像感覺不到了。 「快快,來幫個忙。」醫護兵靠向擔架實施CPR急救,一、二、三、四...邊喊邊做,反覆不斷。醫護兵、帶隊士官及阿鄔的三媳婦,三個人忙做一團。 阿鄔急了,身體縮向門邊,盡量讓出空間,同時把剛才手中的檳榔塞在門邊,取出另一顆後,開始祭起招魂的咒語。「嘎辛僅,艾嘎瞇林,阿拉母,嘎日嘎,嗚入瑪」......。她注意到她師父剛才刻意放慢的手法,阿鄔決定搶時間,在她兒子走完那條路前召回來。 直昇機順著陽光滑過雲層,正準備飛越大武山區,遠遠的大小鬼湖,像兩顆晶亮的藍淚珠兒,滴落在綠鬱的山脈。轟轟的引擎聲蓋過了急救聲,也蓋過阿鄔越來越急的唸咒聲。急救的人冒出了一身汗,阿鄔也濕了一身汗,她覺得腦殼快漲破了,心臟被掏空似的虛。 阿鄔看了一眼擔架上的兒子,心裡一陣酸,淚水直衝眼鼻。她不放心的巡視機艙內,沒有發現任何暗門形成,稍微寬心的喘了口氣。撇頭向窗外,卻見到一個雲層下,她的兒子正快速的向部落的方向滑去,表情一如昨天以前。而剛才在醫院聚集的黑衣女巫,此時卻已經在阿鄔的祖靈屋前等候。她的師父也雜在其中,正抬頭望向阿鄔,平和與安詳。與阿鄔眼神相對,卻像根巨槌一樣,猛力的搥碎阿鄔早已經瀕臨碎裂的心。「嗚.........」阿鄔一聲長泣,頹坐回椅背上,暈了過去。 捏著的檳榔掉出手掌心,在機艙底彈了一下,滾向擔架,停在她兒子包紮過的後腦邊,機身一陣震動後,又滾向另一個門邊。醫護兵移動身子,調整急救姿勢,不留神踩扁了那顆夾著紅丹的檳榔。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急救依然進行。 阿鄔抽動了一下,醒了過來,淚水卻爭相從她闔閉的眼眶冒出,像地下水一般的不停,濕了整臉的皺紋。 「老五走了。」阿鄔顫抖著伸手,想制止他們繼續的急救動作。 「讓他舒服的走吧!」阿鄔低著頭費力的說。醫護兵沒理會,繼續他的急救動作。 「嗚...」阿鄔撇過頭,強忍著不讓聲音發出來。 「我怎麼會忘了喚他上機?嗚...,如果...他會走嗎?嗚...」 「唉,年輕,這麼年輕,嗚...」 阿鄔開始感到疲倦,她承受不住這樣的結果,她救得了別人的小孩,卻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兒子,給祖靈接了去。那樣的無奈,那樣的心傷。 「搭拉芼只是玩笑嗎?嗚...」 「命?是運?是注定?嗚...我一個老婦人...心傷啊...」阿鄔緊閉著嘴,自語。 直昇機繼續向西飛,強大的氣漩快速的拖著飛機滑行,卻拖載不了阿鄔兒子微弱的一口氣,飛越大武山脈。大小鬼湖在雲層下,卻偷偷的擷集所有傷心人克制不住的淚水,而越發悲傷鬱藍。 阿鄔癱軟在座位上,任憑「拉法」裡,用剩的檳榔滾出亂竄。她無力再做任何動作,除了閉起的眼睛不斷奔流的淚水。 「我的兒啊......嗚...」註:一、搭拉芼:卑南語,意指白巫術,舉凡祈福、祝禱、趨邪、去病等都算是白巫術的範圍。二、巴里西:黑巫術,設符咒、放置鎮邪物、法術等。三、卜拉法:新進女巫,法器的啟用儀式,向授旗授槍一樣。四、拉法:隨身置物袋,特別指巫師裝置法器的隨身袋。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製作,所有內容均受智慧財產權及相關法律保護。
基本資訊
- 原始資料連結
- 資料來源
- 主題分類
- 建檔單位
- 作品語文中文
- 地圖
本網站使用Cookies收集資料用於量化統計與分析,以進行服務品質之改善。請點選"接受",若未做任何選擇,或將本視窗關閉,本站預設選擇拒絕。進一步Cookies資料之處理,請參閱本站之隱私權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