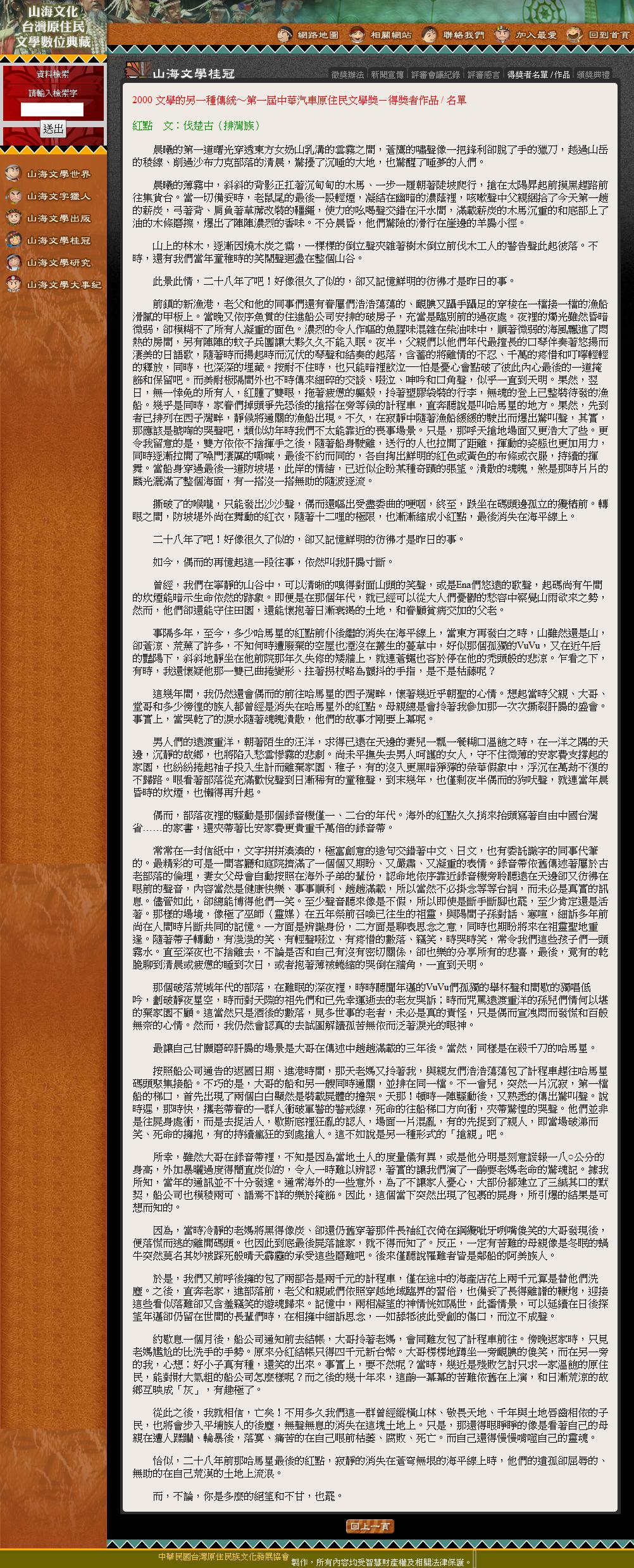跳到主要內容區塊
:::
山海文化 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
山海文化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資料檢索請輸入檢索字2000文學的另一種傳統~第一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得獎者作品/名單紅點 文:伐楚古(排灣族) 晨曦的第一道曙光穿透東方女奶山乳溝的雲霧之間,蒼鷹的嘯聲像一把鋒利卻脫了手的獵刀,越過山岳的稜線、削過沙布力克部落的清晨,驚擾了沉睡的大地,也驚醒了睡夢的人們。 晨曦的薄霧中,斜斜的背影正扛著沉甸甸的木馬、一步一履朝著陡坡爬行,搶在太陽昇起前摸黑趕路前往集貨台。當一切備妥時,老鼠尾的最後一股輕煙,凝結在幽暗的濃蔭裡,咳嗽聲中父親綑拾了今天第一趟的薪炭,弓著背、肩負著草蓆改裝的韁繩,使力的吆喝聲交錯在汗水間,滿載薪炭的木馬沉重的和底部上了油的木條磨擦,爆出了陣陣濃烈的香味。不分晨昏,他們驚險的滑行在崖邊的羊腸小徑。 山上的林木,逐漸因燒木炭之需,一棵棵的倒立聲夾雜著樹木倒立前伐木工人的警告聲此起彼落。不時,還有我們當年童稚時的笑鬧聲迴盪在整個山谷。 此景此情,二十八年了吧!好像很久了似的,卻又記憶鮮明的彷彿才是昨日的事。 前鎮的新漁港,老父和他的同事們還有眷屬們浩浩蕩蕩的、靦腆又躡手躡足的穿梭在一檔接一檔的漁船滑膩的甲板上。當晚又依序魚貫的住進船公司安排的破房子,充當是臨別前的過夜處。夜裡的燭光雖然昏暗微弱,卻模糊不了所有人凝重的面色。濃烈的令人作嘔的魚腥味混雜在柴油味中,順著微弱的海風飄進了悶熱的房間,另有陣陣的蚊子兵團讓大夥久久不能入眠。夜半,父親們以他們年代最擅長的口琴伴奏著悠揚而淒美的日語歌,隨著時而揚起時而沉伏的琴聲和結奏的起落,含蓄的將離情的不忍、千萬的疼惜和叮嚀輕輕的釋放,同時,也深深的埋藏。按耐不住時,也只能暗裡飲泣──怕是憂心會點破了彼此內心最後的一道掩飾和保留吧。而美耐板隔間外也不時傳來細碎的交談、啜泣、呻吟和口角聲,似乎一直到天明。果然,翌日,無一悻免的所有人,紅腫了雙眼,拖著疲憊的軀殼,拎著塑膠袋裝的行李,無魂的登上已整裝待發的漁船。幾乎是同時,家眷們掉頭爭先恐後的搶搭在旁等候的計程車,直奔聽說是叫哈馬星的地方。果然,先到者已排列在西子灣畔,靜候將通關的漁船出現。不久,在寂靜中隨著漁船緩緩的駛出而爆出驚叫聲,其實,那應該是號啕的哭聲吧,類似幼年時我們不太能靠近的喪事場景。只是,那呼天搶地場面又更浩大了些。更令我留意的是,雙方依依不捨揮手之後,隨著船身駛離,送行的人也拉開了距離,揮動的姿態也更加用力,同時逐漸拉開了嗓門淒厲的嘶喊,最後不約而同的,各自掏出鮮明的紅色或黃色的布條或衣服,持續的揮舞。當船身穿過最後一道防坡堤,此岸的情緒,已近似企盼某種奇蹟的張望。潰散的魂魄,煞是那時片片的麟光灑滿了整個海面,有一搭沒一搭無助的隨波逐流。 撕破了的喉嚨,只能發出沙沙聲,偶而還嘔出受盡委曲的哽咽,終至,跌坐在碼頭邊孤立的纜樁前。轉眼之間,防坡堤外尚在舞動的紅衣,隨著十二哩的極限,也漸漸縮成小紅點,最後消失在海平線上。 二十八年了吧!好像很久了似的,卻又記憶鮮明的彷彿才是昨日的事。 如今,偶而的再憶起這一段往事,依然叫我肝腸寸斷。 曾經,我們在寧靜的山谷中,可以清晰的嗅得對面山頭的笑聲,或是Ena們悠遠的歌聲,起碼尚有午間的炊煙能暗示生命依然的跡象。即便是在那個年代,就已經可以從大人們憂鬱的愁容中察覺山雨欲來之勢,然而,他們卻還能守住田園,還能懷抱著日漸衰竭的土地,和眷顧貧病交加的父老。 事隔多年,至今,多少哈馬星的紅點前仆後繼的消失在海平線上,當東方再發白之時,山雖然還是山,卻蒼涼、荒蕪了許多,不知何時遭廢棄的空屋也凐沒在叢生的蔓草中,好似那個孤獨的VuVu,又在近午后的豔陽下,斜斜地靜坐在他前院那年久失修的矮牆上,就連蒼蠅也吝於停在他的禿頭般的悲涼。乍看之下,有時,我還懷疑他那一雙已曲捲變形、拄著拐杖略為顫抖的手指,是不是枯藤呢? 這幾年間,我仍然還會偶而的前往哈馬星的西子灣畔,懷著幾近乎朝聖的心情。想起當時父親、大哥、堂哥和多少徬徨的族人都曾經是消失在哈馬星外的紅點。母親總是會拎著我參加那一次次撕裂肝腸的盛會。事實上,當哭乾了的淚水隨著魂魄潰散,他們的故事才剛要上幕呢。 男人們的遠渡重洋,朝著陌生的汪洋,求得已遠在天邊的妻兒一瓢一餐糊口溫飽之時,在一洋之隅的天邊,沉靜的故鄉,也將陷入愁雲慘霧的悲劇。尚未平撫失去男人呵護的女人,守不住微薄的安家費支撐起的家園,也紛紛捲起袖子投入生計而離棄家園、稚子,有的沒入更黑暗猙獰的榮華假象中,浮沉在萬劫不復的不歸路。眼看著部落從充滿歡悅聲到日漸稀有的童稚聲,到末幾年,也僅剩夜半偶而的狗吠聲,就連當年晨昏時的炊煙,也懶得再升起。 偶而,部落夜裡的騷動是那個錄音機僅一、二台的年代。海外的紅點久久捎來抬頭寫著自由中國台灣省……的家書,還夾帶著比安家費更貴重千萬倍的錄音帶。 常常在一封信紙中,文字拼拼湊湊的,極富創意的造句交錯著中文、日文,也有委託識字的同事代筆的。最精彩的可是一間客廳和庭院擠滿了一個個又期盼、又嚴肅、又凝重的表情。錄音帶依舊傳述著屬於古老部落的倫理,妻女父母會自動按照在海外子弟的輩份,認命地依序靠近錄音機旁聆聽遠在天邊卻又彷彿在眼前的聲音,內容當然是健康快樂、事事順利、趟趟滿載,所以當然不必掛念等等台詞,而未必是真實的訊息。儘管如此,卻總能博得他們一笑。至少聲音聽來像是不假,所以即使是斷手斷腳也罷,至少肯定還是活著。那樣的場境,像極了巫師(靈媒)在五年祭前召喚已往生的祖靈,與陽間子孫對話、寒喧,細訴多年前尚在人間時片斷共同的記憶。一方面是辨識身份,二方面是聊表思念之意,同時也期盼將來在祖靈聖地重逢。隨著帶子轉動,有淺淺的笑、有輕聲啜泣、有疼惜的數落、竊笑,時哭時笑,常令我們這些孩子們一頭霧水。直至深夜也不捨離去,不論是否和自己有沒有密切關係,卻也樂的分享所有的悲喜,最後,竟有的乾脆聊到清晨或疲憊的睡到次日,或者抱著薄被蜷縮的哭倒在牆角,一直到天明。 那個破落荒城年代的部落,在難眠的深夜裡,時時聽聞年邁的VuVu們孤獨的舉杯聲和間歇的獨唱低吟,劃破靜夜星空,時而對天際的祖先們和已先幸運逝去的老友哭訴;時而咒罵遠渡重洋的孫兒們情何以堪的棄家園不顧。這當然只是酒後的數落,見多世事的老者,未必是真的責怪,只是偶而宣洩悶而發慌和百般無奈的心情。然而,我仍然會認真的去試圖解讀孤苦無依而泛著淚光的眼神。 最讓自己甘願磨碎肝腸的場景是大哥在傳述中趟趟滿載的三年後。當然,同樣是在殺千刀的哈馬星。 按照船公司通告的返國日期、進港時間,那天老媽又拎著我,與親友們浩浩蕩蕩包了計程車趕往哈馬星碼頭聚集接船。不巧的是,大哥的船和另一艘同時通關,並排在同一檔。不一會兒,突然一片沉寂,第一檔船的梯口,首先出現了兩個白白顯然是裝載屍體的擔架。天那!頓時一陣騷動後,又熟悉的傳出驚叫聲。說時遲,那時快,攜老帶眷的一群人衝破軍警的警戒線,死命的往船梯口方向衝,夾帶驚惶的哭聲。他們並非是往屍身處衝,而是去捉活人,歇斯底裡狂亂的認人,場面一片混亂,有的先捉到了親人,即當場破涕而笑、死命的擁抱,有的持續瘋狂的到處搶人。這不如說是另一種形式的「搶親」吧。 所幸,雖然大哥在錄音帶裡,不知是因為當地土人的度量儀有異,或是他分明是刻意謊報一八○公分的身高,外加暴曬過度得簡直炭似的,令人一時難以辨認,著實的讓我們演了一齣要老媽老命的驚魂記。據我所知,當年的通訊並不十分發達。通常海外的一些意外,為了不讓家人憂心,大部份都建立了三緘其口的默契,船公司也模稜兩可、語焉不詳的樂於掩飾。因此,這個當下突然出現了包裹的屍身,所引爆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因為,當時冷靜的老媽將黑得像炭、卻還仍舊穿著那件長袖紅衣倚在鋼纜呲牙咧嘴傻笑的大哥發現後,便落慌而逃的離開碼頭。也因此到底最後屍落誰家,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一定有苦難的母親像是冬眠的蝸牛突然莫名其妙被踩死般晴天霹靂的承受這些磨難吧。後來僅聽說罹難者皆是鄰船的阿美族人。 於是,我們又前呼後擁的包了兩部各是兩千元的計程車,僅在途中的海產店花上兩千元算是替他們洗塵。之後,直奔老家,進部落前,老父和親戚們依照穿越地域臨界的習俗,也備妥了長得離譜的鞭炮,迎接這些看似落難卻又含羞竊笑的遊魂歸來。記憶中,兩相凝望的神情恍如隔世,此番情景,可以延續在日後探望年邁卻仍留在世間的長輩們時,在相擁中細訴思念,一如舔牴彼此受創的傷口,而泣不成聲。 約歇息一個月後,船公司通知前去結帳,大哥拎著老媽,會同難友包了計程車前往。傍晚返家時,只見老媽尷尬的比洗手的手勢。原來分紅結帳只得四千元新台幣。大哥楞楞地蹲坐一旁靦腆的傻笑,而在另一旁的我,心想:好小子真有種,還笑的出來。事實上,要不然呢?當時,幾近是殘敗乞討只求一家溫飽的原住民,能對財大氣粗的船公司怎麼樣呢?而之後的幾十年來,這齣一幕幕的苦難依舊在上演,和日漸荒涼的故鄉互映成「灰」,有趣極了。 從此之後,我就相信,亡矣!不用多久我們這一群曾經縱橫山林、敬畏天地、千年與土地唇齒相依的子民,也將會步入平埔族人的後塵,無聲無息的消失在這塊土地上。只是,那還得眼睜睜的像是看著自己的母親在遭人蹂躪、輪暴後,落寞、痛苦的在自己眼前枯萎、腐敗、死亡。而自己還得慢慢啃噬自己的靈魂。 恰似,二十八年前那哈馬星最後的紅點,寂靜的消失在蒼穹無垠的海平線上時,他們的遺孤卻屈辱的、無助的在自己荒漠的土地上流浪。 而,不論,你是多麼的絕望和不甘,也罷。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製作,所有內容均受智慧財產權及相關法律保護。
基本資訊
- 原始資料連結
- 資料來源
- 主題分類
- 建檔單位
- 作品語文中文
- 地圖
本網站使用Cookies收集資料用於量化統計與分析,以進行服務品質之改善。請點選"接受",若未做任何選擇,或將本視窗關閉,本站預設選擇拒絕。進一步Cookies資料之處理,請參閱本站之隱私權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