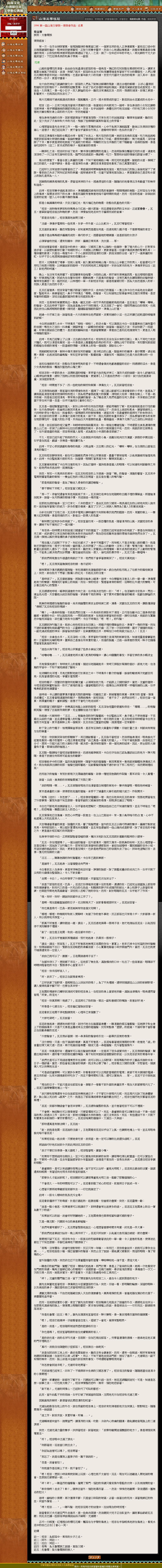跳到主要內容區塊
:::
山海文化 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
山海文化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資料檢索請輸入檢索字1996第一屆山海文學獎-得獎者作品/名單蔡金智族別:太魯閣族得獎感言: 有一次,在月台排隊買票,發現隔壁排的售票窗口前,一個原住民的老人正準備買票。當他從口袋中取出幾張皺摺的舊鈔,眼神突然變得驚慌,正努力用雙手壓平,然後小心地遞給售票員。我看到售票員掛在嘴邊的微笑,以和悅的眼神連同零錢和票遞給了老人;之後,換了一位年近中年的平地人,將光鮮的千元大鈔拋到窗口,下巴拉得長長的和鼻子齊高,一副傲花痕 山風和著櫻花的清香,自由自在地盪漫在部落的每一個角落。嫣紅的花兒妝點在青綠的枝芽上,讓原本籠罩在寒風下的部落,活潑、熱鬧了起來。部落的生活方式和周遭環境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性,人們以櫻花花開的季節來判記一年的開始,也是計算年齡大小的依據。世世代代謹守大自然的規律,溶入其中,是自然界的一份子,更是守護者。 在大自然神祕又詭譎的變化中,部落的人們為了對無法解釋的現象,提出合理的解釋,以求心靈得到慰藉和安定的情形下,長時間的經驗累積,形成了各式各樣的神話和傳說,更甚而演變成習俗或是禁忌。而這些,久而傳之,像一粒小石子,投入靜謐的池中,雖然沒有湧起巨浪,然而,微緩的漣漪,卻傳之更遠,影響更大,也就因此而生活化了。 幾片花瓣拗不過疾風頑皮的撩弄,隨風飄飛,正巧,透木板築成的窗口,散落到由水泥圍成的水池中。 妲吉(註一)正用力地搓洗著被汗浸黃的衣服,每當她右手向前用力一搓時,背在身後的小女兒也順勢往前伸掉,幾乎要躍過她的頭部而飛出去。然後,右手回搓時,身體也技巧地往回縮,巧妙地又將小女兒安穩地伏躺在繫於身上袋形的大花布,安然地睡著。 堆在身旁洗過的衣物,因家裡窮得捨不得買清潔劑,只有多用力來回搓揉著,顯得有些皺黃。雖然如此,至少洗去了汗臭味和大半的污泥,殘餘了些糢糊的圖案和著泥土的芳香。 心裡想著這是先生辛苦工作,一點一滴努力累積拼成地,心中不免再次湧起踏實、勤儉以及得到收穫的窩心。這樣子,就已經足夠了,更不會在乎當掛在竹架上,遠看時好像同一色系的衣服了。 妲吉正準備用木製的水瓢搯水時,發現了水池上,幾片悠然的花瓣。她抓住池角的泥牆,吃力地挺起略微肥胖部落婦女特徵的身軀。發麻的雙腿,不聽使喚似的喪失了功能,還微微地顫抖,無力地搖晃,深怕會跨了下來。雙手更是使勁地鼓起了充滿勁力的青筋,明顯的伏在左手腕的刀痕下蠕動著。扭曲的臉頰,像是偷吃到阿外(註二)家未成熟的梅子,極度痛苦的表情。 一陣掙扎之後,妲吉終於站了起來,雙手撐在腰際間的池牆上,然後將臉橫在飄著花兒的水面,滿意地深深吸了一大口含有花香味的空氣,腦門兒迅速感到一陣舒暢,吃力,緊張和糾結的情緒也跟著冰釋了。 幾分的愜意下,看著水面上美麗的花瓣,不知不覺地嘟起小嘴,將花兒吹起盪開,皺起的水面,糢糊了自己的面孔。水面平靜後,像是一面澄淨的水鏡,讓妲吉清清楚楚地看見了自己真實的面孔。 已經好久沒有這麼仔細看著自己了,常感覺到時間無聲無息地溜走,竟然在自己的臉上偷偷地留下了痕跡。看到自己失去了同年紀該有的美麗,超勞過度辛累,也毫不留情地寫在臉上,更是驚訝自己是否和水面上的臉孔是同為一人。 因藥劑而頗具規模的乳房,浸著溼淋淋的汗水,透過浸溼的衣服,隱隱約約地看得出浮長動盪下的無奈和滄桑。 此時,妲吉用雙手端起清涼的水,準備點醒因疲倦而惚晃的意識時,眼睛視線的焦點,正好落在左手腕上的傷痕。指間滲流而下的水滴,像是刻漏般有意無意地暗示著時間的飛逝。然而,妲吉的思緒,卻倒回到從前的記憶,墜入心中永難平撫的傷痛……。 那是小鳥歸巢的時候,天空泛著紅光,幾片橘紅色的晚霞,妝點在乳藍色的天際。 「妲吉,我昨晚有夢到和妳媽媽合力扛起一頭大肥豬,而且還看到我們的玉米田,正結實纍纍。」瓦旦‧達寧對著妲吉說出昨晚的夢。然後,神情愉悅地走向竹子編築而成的倉庫。 「那是吉兆哦!」妲吉猜測地詢問父親。 「沒錯,準備手電筒和一些用具,多穿一件外套,山上比較冷。」瓦旦叮嚀著妲吉。 瓦旦進到倉庫後,雖然有點昏暗,卻知道東西是擺在何處,迅速地裝入籠子裡,不需要視覺的肯定。 這籠子是由媽媽親手編織而成的,精巧的手工,透露著她的聰穎慧,這是部落的女孩子 必須學會的技能,還有如織布、持家、編織日常用具、洗衣服……等。 妲吉回憶著母親,是部落中的美女,據說,父親用三隻大山豬和一些獵物,費了極大的心力,打敗眾多追求者,以誠懇和勤勞打動了母親的芳心。木親臉上的黥紋,更象徵著是一位謹守傳統美德的賢妻良母,一種榮耀的象徵。只是在一場意外中,不小心踩到因雨溼滑的石頭,跌落深淵的谷底,留下了一道美麗的彩虹,似乎不甘心地想再接續她該有的燦爛生命。 那天,太陽像做了壞事,怕被人發現,躲入廣漠的峻峭山嶺。而在山上辛勤工作的男人,趁著還可以不用吃力地張大眼睛,以辨識回家的路時,不約而同地將工具整理好,安放在原來的地方,準備享受拉白(註三)對他們的呵護。 晚上,在沒有月亮照耀下,部落顯得有些暗闇。冷勁的山風,將芒草吹得東搖西晃,發出嗦嗦的摩擦聲,好像酒鬼巴萬‧阿威先生在豐年祭時,酣醉起舞。只是傳來的聲音,沒有巴萬先生腰際間的鈴聲熱鬧,顯得有些蕭瑟。但,縱然如此,山林裡的一草一木對妲吉來說,都是相當親切的,因為大自然是族人的家,而族人更是大自然的子民。 瓦旦扛著獵具,妲吉背著竹籠子跟著父親的步伐,走向自己的獵區。一隻土狗卡白也本能地走在最前面,豎起耳朵,高舉著尾巴。鼻子不時傳出「嘶嘶」的聲音,可以知道牠正聚精會神地注意四周環境,是否有動物的蹤跡,深怕沒能盡到獵狗的責任而感到恥辱。 突然,從側旁的草叢間飛出一隻鳥,離瓦旦前一條竹竿長的距離前飛越而過,並且發出「嗶嘰、嗶嘰」的聲音。瓦旦此時停下腳步,因為這是鳥占中不祥的預兆。瓦旦深思了一會兒,隨即閃過拉白的微笑,也就因此放任山風將剛剛的憂慮一掃而逝,繼續踏著強韌的腳步,準備上山打獵。 越過一片芒草之後,接著就是一大片的樹林在他們面前。流貫而過的小溪,也正好讓已經乾澀的喉嚨得到舒解。 卡白將舌頭浸入水中,不時傳來「啪啦,啪啦!」的汲水聲,可以猜測出卡白一定是讚美自己擁有靈巧的舌頭。喝完水之後抖一抖身軀,頭腳伸直,一副暢快的感覺。接著搖一搖尾巴之後,來回快跑了一段距離,好像在測試自己的體力,是否達到巔峰狀態。牠舔著雙雙腿,得意自己是如此地強健有力,更是主人眼中稱職的獵狗。 此時,月亮已經攀上了山頂,泛出銀白色的月光。妲吉和瓦旦坐在溪水旁的石頭上,倆人不用吃力地放大瞳孔,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片像是披上層墨藍色的柔紗的月夜。遠眺山坳下的部落,有如嬰兒般甜甜的酣睡在母親的懷裡,一股溫暖的悸動,流貫身上的每一個細胞,服貼在心中。 微風輕輕地吹拂,樹林中傳來清新悅耳的韻聲;清冷帆白的山嵐,隨著美妙的韻律,曼妙開閤,婆娑起舞。偶爾,此起彼落的蟲鳴聲,有如豆芽音符般,點耀起聲,清脆悅耳,強調自己也是大自然舞台的一份子。 這如仙境般的月夜,妝點在月娘旁明亮的星子,不時還會頑皮地劃過墨藍的夜紗。而緩緩的溪水,像是少女柔柔的髮絲,飄逸灰藍色的山嶺之間。 妲吉汲取一手掌的泉水,滋潤乾澀的喉嚨,享受著大自然鬼斧神工,渾然天成的細緻。這令人舒適而且心暢神怡的情景,緩和了因爬山而急促的喘息聲,更覺得│人│只是自然界的一小部份,對大自然莫測奇麗,深深感到敬畏。 「妲吉,時間差不多了,找一些乾枯的樹枝和樹葉,準備生火。」瓦旦對著妲吉說。 瓦旦微微抬起頭,張望著四周的環境和地形。選擇了一個三面山脈都可以清楚看到的小平地。這是為了讓飛鼠能清楚地看到燃燒時熊熊煜火。因為牠們會張起寬大的膜翼,滑翔到火焰旁,棲息在樹上,不是一起來取暖,而是發出短促清亮、帶有幾分詭譎的聲音,為了嚇走侵入牠們地盤的任何入侵者,來保衛自己的家園不受任何干擾。但是,似乎只適用於│動物│而已。 瓦旦是一個經驗豐富的獵人,對於山林中的任何自然現象,都能明確的了解。他知道飛鼠是夜行性的動物,在天色微暗時,就會爬出樹洞來覓食。牠們先從山上飛到山下,然後往上追逐和覓食,順著稜線而上,大約時針停在十點左右,就會尋找一個視線良好的樹梢棲息,遠望四周。但最重要的是將吃下的食物消化掉,空出部份的空間,以準備之後再次的覓食。接下來,就比先前的食量來得多了,因為要儲存更多的食物在牠那彈性好、容量大的肚子裡,來供給白天所需要的能量,養精蓄銳,準備予太陽下山之後的山林追逐。 但是,自從部落的祖父輩們,年輕時被林務局雇用後,和一堆發出嘈雜怪聲,不時還冒出臭氣濃濁的機器上山之後,砍倒了山樹林中比拉白的腰還粗的樹木,許多的大樹被運往平地。然而,飛鼠的家也被帶走了,在外面遊盪的飛鼠,很容易被獵人發現,成為配佐小米酒的最佳菜餚了。 不久,妲吉已經升起了熊熊的烈火,火舌像脫手而飛的小鳥,逃難似地向四方湧竄,誇張的手舞足蹈,似乎是在挑逗、戲謔,彷彿是一種挑釁行為。 此時,不甘心受到調戲和侮辱的飛鼠,火眼金睛,泛出慄人的紅光,「嗶咻,嗶咻」在左側的山面發出清亮的聲日。 瓦旦和妲吉靜悄悄地,躲在可以隱藏他們身子的山芋葉後面,盡量不要被發現,以免被識破而愴惶地飛走。此時,卡白豎起葉片般的耳朵,抬著頭,眼睛盯著某個方向,顯得英氣逼人。 瓦旦驚覺地察覺了卡白所注意的地方。因為打獵時,獵狗就像是獵人的眼睛,可以知道和判斷動物之所在,趁牠們尚未逃走時,捉捕就擒。 突然,有如一大塊長形的黑布,從瓦旦和妲吉的上方掠過。接著「唰」的聲音,清脆的響著。瓦旦用手電筒照耀著晃動的樹梢,一雙金紅色的火眼正怒視著,並且發生懼人的鳴叫聲。 「那是飛鼠的聲音,是為了嚇走入侵者的抗議恐嚇聲。」 「要不要射下來呢?」妲吉望著父親瓦旦。 「等一下,待會兒還會有其他飛鼠飛下來。」瓦旦倒也老神在在地隨勢取出籠子裡的彈藥盒,將獵槍清拭乾淨,接著一系列熟練的裝填子彈,來迎接這一場狩獵。 從那把生銹的槍身,至少已有七、八年的歷史了,是由瓦旦的父親用一塊長滿花生的山坡地向別人換來的。這把槍有著強大的威力,許多的豐功偉業,奠定了父子二人被族人稱羨為│獵人│的幕後英雄。 分針往右跨了五格之後,瓦旦將手電筒以順時鐘的方向照射尋找牠們的蹤跡。然而,周圍的樹上,一雙雙火紅的眼睛,像是燃燒的烈火,散發出一股慄人的氛圍。 「樹林間已經有許多的飛鼠了。」妲吉望著四周,一股恐懼的氣息,隨著清冽的山風,流竄妲吉的身旁,讓她不知不覺地打了一個冷顫。 「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到這個父親遺留下來的獵區了,沒想到已經有這麼多的飛鼠了。要是在林務局沒來之前,或許還可以有足夠的樹洞和食物來供給牠們,現在恐怕很難有這樣的環境來維持牠們生存了。」瓦旦摸一摸被山風吹得發癢的鼻子感慨地呢喃著。 「現在獵人已經剩下不多了,年紀也都大了,身手不再靈巧了,而年輕人不是沒有獵人般的體力,就是缺乏狩獵的技術,幾乎少有年輕一輩的獵人出來狩獵了。而山上的動物,沒有人干擾,繁殖力強,幾年後,數量比部落的人還多了。但是,近幾年來,雖然有人受雇到山林裡種樹,樹木成長的速度比不上動物的繁殖力,不能馬上解決牠們生計問題,難怪會鋌而走險,侵入、偷吃我的農作物。」瓦旦又是一陣噓唏。 「那我們將幾隻在外遊盪的飛鼠打下來,牠們就不會爭著擠樹洞了。」妲吉天真地說。 「嗯!」瓦旦微笑著撫摸妲吉的頭,表示認同。 樹林間再次傳來颼颼的摩擦聲,有如漲潮的浪濤聲節節升高。銀白色的弦月跳上了右前方的扁柏樹頂上,突然,鉤在弦月下閃著二點懾人的紅光,引起瓦旦的注意。 「是時候了。」瓦旦舉起獵槍,將臉靠在槍身上瞄準。這時,卡白機警地注意主人的一舉一動,準備彈起有力的雙腿,眼睛死盯著樹上的飛鼠。而在一旁的妲吉,緊握著身旁的樹枝,從睜的比牛還大的雙眼,可以看出她內心的緊張。 瓦旦緩緩地呼吸,瞄準到滿意的方向之後,右手指決定性的一扣。「呼!」在洹寒的冷空氣中,閃出一道金色光煜,天空響起尖銳巨裂的槍聲,穿過看不見的黑暗,留下震耳欲聾的聲音的轍痕,弧劃在靜謐的天際。 刺鼻的硝煙趕在槍聲的餘音,尚未被幽闇的黑夜全部吸掉之前,湧暴、流竄在瓦旦的四周,擴散瀰漫著「糢糊了瓦旦和妲吉的視線。 「唰!」一連串碎裂聲,引起他們的注意。一片長條形的黑影向下滑落,正巧落在離卡白二個身長的距離前。敏捷的卡白,好比脫弦而飛,一閃即逝的速度,在飛鼠快要著地的剎那,撲咬住飛鼠。飛鼠的左翼雖然中槍而淌著血,卻也奮力地和卡白搏鬥,卡白不時傳出「嗯、嗯!」的叫聲。 瓦旦聽到狗叫聲之後,就放心地和妲吉坐在石頭上,將籠子裡的彈藥盒取出,準備下一場的狩獵。而在不遠的草叢裡和飛鼠纏鬥的卡白,以靈敏的身手和銳利的犬齒,花了放一次尿的時間,擺平了頑強的飛鼠。一副充滿成就感的神采,踩著愉快的腳步,從草叢間跑出來,將啣在口中的飛鼠交給主人||瓦旦。 「妲吉,去拿些水來。」瓦旦深吸一口氣,享受著取代硝煙之後清冽的新鮮空氣,知道祖靈是眷顧著他的。泛著勝利光輝的眼神,讚美自己是個名符其實的獵人,俊逸的臉龐,泛起一絲得意的微笑,眸子也隱隱閃著意氣風發的神采。 「這些水夠不夠?」妲吉用山芋葉盛了些泉水拿給父親。 「咕嚕咕嚕……。」瓦旦滿意地將水灌入乾渴的喉嚨中,讓心中翻騰的喜悅,伴著甘美的泉水暢流全身。 月亮慢慢地緩行,有時被天上的雲層,強迫似地隱藏起來,有時又掙脫於稀薄的雲紗,銀亮大地,在浩瀚的宇宙中,不知不覺地締造了藝術。 在流轉的光河裡,月亮也默默地航行於黑夜之中。不時傳來十數次的槍響,餘音的轍痕再次地劃空而飛,托曳著連煜的光弧,爭耀於星際間。 妲吉的籠子,因豐收的獵物而愈顯沈重,必須再加把力氣,才能跟上父親的腳步。當然,沈重的獵物,令妲吉感到興奮和愉快,取代了疲倦的意念,邁著輕鬆的步伐,縱橫在山林原野間。呼嘯而過的山風,似乎鳴奏凱歌般地頌讚著。 這時候,半山腰的雞寮傳來響徹天際的雞啼聲,如離弦之箭,刺破層層的黑幕,使東方的雲層,慢慢染成暈紅。瓦旦看著裝滿獵物的籠子,微揚起嘴角,對妲吉說:「差不多了,我們回去吧!」妲吉也聳一聳肩,將厚重的籠子,重新調整,這樣才不會吃力地走回家。 妲吉跟著父親的腳步,快樂滿足地踏上回家的路程,瓦旦深信祖靈的愛護和保佑,「嘿嘿……」的幾聲朗笑聲。領悟了出發前所做的夢,完全應驗在這次打獵中。 快越過一片樹林時,「汪汪……」幾聲急促的狗叫聲響起,卡白豎起尖耳,鼻子朝上不停地嗅著,不但露出尖銳的犬齒,並且還帶著懼人的吠聲,似乎有某種東西,吸引牠的注意。瓦旦和妲吉同時朝著卡白所注意的方向望著,原來是樹幹上有一個樹洞,瓦旦依自己豐富的經驗,推測裡面一定有動物。 取下背上的竹籠子,檢視彈藥盒等容具,是否有足夠的火藥量和子彈數。仔細打量之後,判斷尚有兩發左右的藥量。 「妲吉,妳到樹洞背後的那顆樹下,用石頭敲擊著。」瓦旦指示著妲吉,然後將槍身清拭,眼角餘光不經意地看到一籠子的獵物。心裡正得意地想著「自己真是一個偉大的獵人」,不知不覺地膨脹、自傲地忘了分寸,想用一次超大威力的火藥和子彈,解決那一隻待宰的獵物,做一個完美的結束。因此,將全部的火藥量和子量,裝填在銹的槍膛上。 瓦旦點一點頭暗示著妲吉敲擊樹幹後,迅速地瞄準樹洞。卡白也守在自己認為應該站立的地方。睜大眼睛,像是不放過任何即將可能發生的動靜。 妲吉舉起手中的石頭,猛然地搥著樹幹,隨著乍起的碰撞聲,樹洞果真有一隻飛鼠被驚醒地準備逃之夭夭。就在飛鼠探出頭的剎那,槍聲也隨即響起。從敲擊聲到槍聲不過秒針往下移二格而已,條然間硝煙紛飛。 然而這次的槍聲,有別於前幾次沈厚幽遠的韻聲,卻像一種短促急躁的炸裂聲,震耳欲裂,令人驚懼。 接著,尖銳、崩潰般的哀嚎聲震憾了天際之間。 「我的眼睛,啊……。」瓦旦若隱若現地伏在漫著雪白硝煙的草地中,雙手摀著眼,嘶裂地吶喊著。 原來是過量的火藥,使得那把老舊的獵槍,承受不了過量的火藥引起的強大威力,炸裂開來。 「塔瑪(註四),你怎麼了……!」妲吉像被電觸到一樣,飛也似地奔向瓦旦的身旁,慌張地問著發生了什麼事情,驚慌失措不知怎麼辦,看著受創的父親痛苦的表情,把眼淚也逼出了眼眶。 卡白也不斷地用舌頭舔著主人,似乎著急地想幫忙,想挽回些自己也不知道的驚慌。並且不時發出「嗯嗯!」的悲鳴聲,顯露出對主人的忠心。 瓦旦慢慢地忍住傷痛,突然心中閃著一股意念,在上山之路途中,有一隻小鳥所暗示的占意,心中不免感嘆上天如此捉弄人……。 天空積續著厚重的黑雲,陰霾的天氣,響了幾聲悶雷,窗內的瓦旦正以精巧熟練的雙手,編織竹製家庭用具。有時部落的人,常以超於實價地向他購買,並且有些還會附一些山豬肉或是野菜,除了肯定他的手藝之外,更是基於相互幫忙的同胞愛。 在身旁守候的卡白,正將前腳墊著昏睡的頭,懶洋洋地趴在瓦旦因疏於運動而鬆垮的小腿旁。 「瓦旦,你在裡面嗎?」一個尖細的聲音,從外面傳來,隨即又傳來一股刺鼻的粉味。瓦旦心裡想著一定是位婦女。因為除了尖叫聲之外,那有別花的清香味的濃郁氣味,曾經在結婚時,聞到風騷的吉央小姐,所塗抹過的飾品相似。因此,更肯定是位婦女。也許是她們對自己的容貌失去了信心,拼命地塗鴨打扮,活像一隻花枝招展的火雞。 「汪汪……」陣陣急躁的狗吠聲響起。卡白早已跑到車前。 「是誰呀!」瓦旦起身,沿著牆壁走向門旁。 卡白看到主人在身旁,更是有恃無恐地狂吠著,猙獰的臉部,除了擠壓成疊狀的皮肉之外,似乎只剩下尖利的太齒槙在整個臉上,令人不敢妄動。 「走開,卡白!」卡白好像受了什麼委屈般,夾著尾巴伏在床沿下。 「我是下部落的巫泥‧巴桑。」巫泥打扮得極其炫耀十足的氣勢,濃濃的妝,已經完全遮蓋臉上部落特有的健康膚色,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白的化妝品,和黝黑的脖子形成強烈的對比。身上和脖子上掛著的項鍊,也裝腔作勢地亮晃搖動著,深怕別人忽略了她的存在。然而,對於眼瞎的瓦旦,似乎起不了作用。 「哦,妳好,妳好,聽說妳到都市去工作了?」 「是啊,現在距離聖誕節的日子,也沒剩幾天了,回家看看親朋好友。」巫泥回答著。 「妳也真是乖巧,巴桑一更很高興有妳這個女兒啊!」 「哪裡,哪裡。昨晚剛好和家人閒聊時,知道了你的意外事故,反正部落也只有幾十戶,大家都像一家人,所以就特地來探望。」 「那真不好意思,讓妳跑這一趟,請坐。」瓦旦迅速地摸尋一張椅子後,急忙地推給巫泥坐,以免因招待不周而顯得不禮貌。 「對了,這位是王老闆,和我一起從都市來的。」 「啊!」瓦旦似乎意識到某種錯誤,慌忙地起身,找尋另一張椅子。 「請坐,請坐,別客氣!」瓦旦不好意思地無視王老闆的存在。事實上,他早已被卡白兇猛的狗吠聲嚇住,怕得話都說不出口,緊跟在巫泥略肥的身軀後面,小心翼翼地踮著小碎步跨進門內。當然,瓦旦也就更不曉得還有另一位客人。 「我自己就可以了,謝謝。」王老闆接過椅子坐下。 「在都市待久了,想到鄉下來玩。」從他那了無生氣,滿臉橫肉的口中,吐出了一些客套話,眼睛卻不時瞟向瞪著他的卡白,緊張得手心直冒冷汗。 「妲吉,快來招呼客人!」 「好,我來了。」妲吉正在廚房煮東西。 「正好我煮了些野菜,是剛剛從山上採回來的哦!」為了不失禮貌,還特別強調從山上採的新鮮野菜,讓人覺得就算手藝不好,也要念其辛勞。 王老闆的視線早已轉移到清純可愛的妲吉身上,在妲吉的身上貪婪地移動。滿臉油滑橫肉,眼角還閃著發現「好貨」的淫光。 「妲吉,妳真乖啊!幾歲了?」巫泥將化了妝的臉,裝出一副和善親切的嘴臉,故意討好她。 「好像是十七歲左右。」妲吉羞紅著臉回答著。 巫泥看到王老闆不停地點頭微笑,心裡早已有個數了。 「大家吃菜吧。」瓦旦說著。 巫泥故意起身,緩緩地向前夾菜,卻技巧地左右搖擺著身體,一陣清脆的綴玉撞擊聲,從她脖子和全身上下的綴飾傳來。只是不太像是金屬或珠玉沈穩的碰撞聲,反而有點像「塑膠」的感覺。不過好像不會影響正在扭動身軀的巫泥。 「什麼聲音?」瓦旦微斜著頭,被一串清裂的聲音吸引住,一副尋找答案的表情。 「沒什麼啦,只是一些不值錢的項鍊,真是不好意思。」巫泥暗喜著達到預期的效果,故意把「錢」的音量拉得又高又遠。然後,再次地搖扭著身體,隨後又是一串碰撞聲,充斥著整個房內。 「巫泥,妳真是好命,還擁有可以發出聲音的項鍊,一定是用了很多錢買來的。」瓦旦微弱的聲調,顯露出幾許無奈。還好看不到那張炫耀的嘴臉,真不知如何面對這樣酸窮的家庭,以及妲吉該有的青春年華。 「我們也是可以不用錢這種東西來生活啊,我可以到山上採野菜。用塔瑪製作的手工藝品來換取米食,日子一樣舒適。當然,那些會發出聲音的項鍊,就沒有必要了嘛!」妲吉看出父親的落寞,安慰著他,強調倆人可以快樂地生活。 「可是錢很重要啊,可以買許多東西,你看看我家可以出現歌星唱歌的電視;煮飯不用木頭燒的電鍋,煮出來的飯,比用木頭燒煮的好吃多了,而且不費時間和力氣;還可以買魚肉……等。」巫泥不甘示弱地說著。 「現在的日子,不能只是活在部落社會,像瞎子一樣看不到外面的美麗世界。現在大家都要現代化了。」巫泥又語帶雙關地補上一句。 「我只要和塔瑪還有卡白在這部落快樂地過日子,才不管它什麼現代化呢,而且現代化除了把身體變肥,臉上黏上死白的﹃面具﹄之外,就是忘了部落傳統尊敬長輩的觀念而已。」妲吉也強烈地反擊著巫泥的無禮。 「巫泥,到都市賺錢會不會很辛苦啊!」瓦旦緩和繃緊的氣氛,並示意著妲吉不可以不禮貌。 「不會啊,無經驗也可以慢慢學習,只要習慣就可以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賺很多錢。不像一些部落的男人到遠洋工作,回來之後,那被太陽曬成木炭的顏色,錢又沒有我多。而且,有些還回不來。只剩下和寶貴生命對換的一筆安家費而已。」巫泥從暗黃的齒縫中,又溜出一大串話。 「那妳還真是有辦法啊!」瓦旦說。 「對,我就是老闆,巫泥說的沒錯!」王老闆看到巫泥似乎佔了上風,也順勢地補上一句,並且用眼角餘光暗示著巫泥。 「如果妲吉能一起去做,只要她肯吃苦,我保證,她一定可以賺的比我還多錢呢!」巫泥 將話鋒巧妙地扣回到今天到此拜訪瓦旦的目的。 「我才不要打扮得像一隻火雞呢!」妲吉瞪著眼,撇著小嘴。 「如果妳不想將錢用在裝扮上,至少可以買魚肉和新鮮的食物,讓塔瑪吃得比較豐盛。也可以買些衣服,不要同一件衣服,從去年聖誕節穿到今年聖誕節,這樣是不衛生的,容易生疾病。」巫泥逮住妲吉孝順的弱點。 「最重要的,是可以有錢讓妳塔瑪治病,說不定可以治好,重見光明呢!」巫泥祭出最後的法寶,語調還柔和輕揚,有著迎向光明未來的希望的語氣。 「那要多久才能回家呢?」妲吉聽到可以讓塔瑪重見光明之後,鬆動了那顆倔強的心。 「不會很久,一年的時間就可以了。」巫泥看到鬆了戒心的妲吉,故意將日子說成一年, 心想著只要將她帶離部落到都市去,一切也就搞定了。 此時,一股令人曖昧的氣氛充斥全場。 巫泥看到僵持不下的場面,於是打鐵趁熱,趁勝追擊,怕會前功盡棄,突然,巫泥靈機一動: 「這是一點小意思,如果覺得可以就請收下,到時還會有比這更多的錢。」巫泥從王老闆身上取出一筆為數不少的錢。 「如果說可以的話,我會好好照顧她的。」王老闆表情也裝得相當和藹可親的樣子。 又是一陣沈默,只聽到卡白的鼻息鼾睡聲。 「我們考慮考慮好了。」瓦旦悶著緊張地說出,心裡想著需要時間來考慮,終究是一件大事。 「那我們把這筆錢交給你,晚上再來好了。」巫泥只好回家,以免逼太急而漏出破綻,前功盡棄。 房間裡只留下瓦旦、妲吉和卡白,一股莫名的愁緒牽動著彼此的一舉一動,令人窒息的氣息,使得彼此都忘了不知怎麼辦,手腳也痲痺地不聽使喚了。 「塔瑪,沒有關係,我會吃苦耐勞的,反正只有一年嘛,一年而已,很快就會回來。我就可以帶你去治病……。」妲吉愈說愈小聲,強忍著顫抖的聲音,突然止住了說話,避免讓父親看到,微溼的眼眶,傷了塔瑪的心。 窗外陰霾的天際,突然終也忍不住厚重壓抑著的雲層,嘩啦嘩啦地一瀉千里,浸溼大地。 一陣急切的敲門聲,驚醒了妲吉,機械式地起身,將門打開,像是上了發條的玩偶。她再一次地看到守在門前的保鏢,嘴角泛著鮮紅噁心的檳榔汁。後面跟著一位精力過剩、尋求發洩的嫖客,準備進行一次又一次的交易。然而,她既非買方,更不是賣方,只是交易過程中的工具而已。 「砰!」沈重的關門聲之後,留下了嫖客謝先生和妲吉二人,處在令人感到罪惡的地方。 謝先生興奮地望著妲吉,準備做出令亞當墮落的行為。突然,仔細一看,那明顯的輪廓,深邃的眼眸,以及高挺的鼻子,應該是和自己流著相同的血液的族。 濃膩沈厚的粉脂,不自然地隱藏住族人天生的健康膚色。頗具規模的乳房,害羞地隱在薄紗的衣服下,病懨懨地垂吊著。 然而,從她那結實的小腿,肯定了謝先生的懷疑。妲吉職業化地脫去了遮羞的外衣,緩緩地坐在床沿。在那張充滿疲倦的臉上,慢慢閤上眼睫的霎那,原本堵在喉嚨上的話,像是被舌尖一一勾引而出,斷線般珠落滾滾。 「妳是托魯閣(註五)嗎?」謝先生猜測地望著妲吉,睜大雙眼,像一隻夜裡尋找獵物的貓頭鷹。 「嗯!」妲吉打起精神,仔細看著這位客人,遲疑了一會兒,覺得有點眼熟。 「是的,我是。」妲吉隨即被這熟悉的腔調吸引住。 「你也是嗎?」妲吉望著眼前的這位皮膚黝黑的客人。 「是的我也是。我的名字叫尤道‧伍塔斯,住在巴幾拉部落。」夾帶著濃濁的酒精,一連串地從他玄黃的門牙裡跳出。 「真巧,我就住在隔壁的沙亞部落!」妲吉擠出一絲乾笑。 「我是在附近的工地上班,最近老闆發薪水,雖然沒有全額拿到,然而,還有一些剩錢,剛好有意無意地聽到同事說過,在這兒可以做﹃好事﹄。所以,不知不覺地走到店門前,被拉了進來。」尤道裝出一副不知情的無奈,然而,臉上卻是洋溢著找到答案的喜悅,不時還瞇著雙眼微笑著。 「妳怎麼會到這來呢?」尤道好奇地問著。 「來到這裡已經有三、四年了。不曉得家中生病的父親怎樣了。」妲吉低沈的聲音,隱隱迴盪在這清冷的小房間裡。 「當時,家遭變故,對都市了解不多,只聽說可以賺大錢。後來,被巫泥誘騙到這兒。可是,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之後,一切也就太晚了。」妲吉神情黯然悲吟,無奈、憤怒地悲訴著。 「對不起!」尤道的同情心,已經取代了可恥的獸慾。 此刻,窗外紛亂不安的雨絲,似乎打破了玻璃窗的阻隔,沈悶地充斥在妲吉和尤道之間。 因風搖曳的樹枝,象徵著彼此間悲淒的怒吼著。 尤道拾起散落在地上的外衣,披在受創的妲吉身上。妲吉終有如潰堤般地伏在床頭上,默默啜泣,隱隱間傳來一絲話語: 「這工作,對我來說,其實好痛,好痛……。」 尤道轉身面向窗外,推開窗門,讓凜冽的冷風,吹散、冷卻內心熱痛的翻湧,避免讓她發現臉上的二道淚痕。 突然,尤道充滿力量的雙手,扶持著妲吉,對著她說:「我帶妳離開這個醜惡的地方!」像是領悟到某種意念。 「好!」妲吉眼中泛滿了淚光。 「妳跟著我,從這窗口爬出去?」 「你認為這樣可以嗎?」妲吉問著。 「別忘了,我是在鷹架上蓋房子的,難不倒我的。」 「但是,我會害怕!」 「妳就當作是從樹上下來,就不會怕了。」 「嗯!妲吉,想到小時候常爬到樹上玩耍,心裡也就不太害怕。況且,現在可以逃離這人間地獄的機會,怎麼說也都要試一試……。 「砰!砰!」一陣猛烈的撞擊聲,撞開了房門,惱怒的保鏢只看到房內零亂的衣物,以及被推開的窗。 「幹你娘咧!走去了!幹!」頭伸出窗外,憤怒地尋找著……。然後,悻悻然地離開,背後還跟一團無名的怒火。 這時,幽暗的小房間,再次獲得平靜,只是窗口碎裂的玻璃,沾著一絲蒼白的死肉,淌著幾鮮紅的熱血,向窗外揮發……。 「喂!妲吉……。」一陣叫聲,把妲吉從剛才的回憶中,拉回現在的時刻裡。 接著看到丈夫尤道從門外走進來,提一些魚肉菜類。然後聽到大兒子正在臥室內,講故事給爺爺瓦旦聽;而瓦旦也講一些部落神話傳說給孫子蘇剛‧尤道聽。 正巧一片輕薄,紅裡透白的櫻花花瓣,飄落在左手臂的傷痕上,妲吉右手指輕柔地按在傷痕上,看見水泥中的自己正在││會心一笑。註釋註一:妲吉:為部落中,常用的女子之名。註二:阿外:同註一。註三:拉白:同註一。註四:塔瑪:為太魯閣族之話語,意指父親。註五:托魯閣:指太魯閣族的族人。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製作,所有內容均受智慧財產權及相關法律保護。
基本資訊
- 原始資料連結
- 資料來源
- 主題分類
- 建檔單位
- 作品語文中文
- 地圖
本網站使用Cookies收集資料用於量化統計與分析,以進行服務品質之改善。請點選"接受",若未做任何選擇,或將本視窗關閉,本站預設選擇拒絕。進一步Cookies資料之處理,請參閱本站之隱私權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