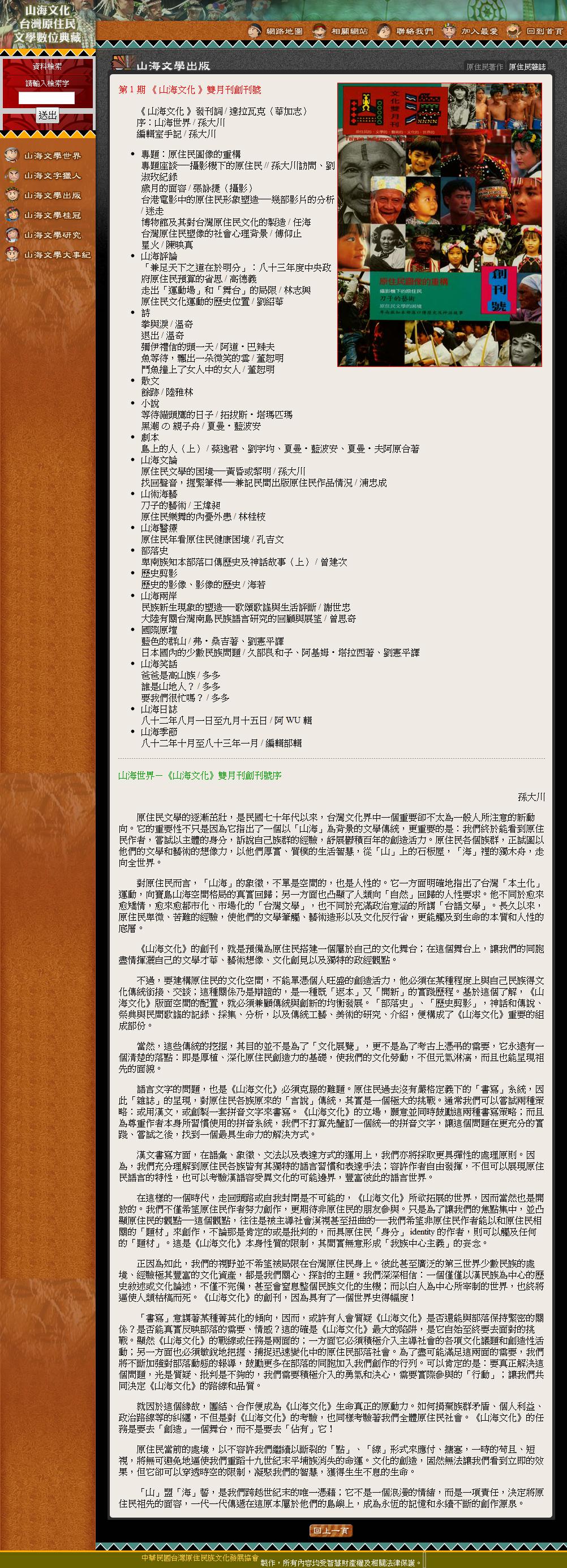跳到主要內容區塊
:::
山海文化 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
山海文化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資料檢索請輸入檢索字第1期《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 《山海文化》發刊詞/達拉瓦克(華加志) 序:山海世界/孫大川 編輯室手記/孫大川專題:原住民圖像的重構專題座談──攝影機下的原住民//孫大川訪問、劉淑玫紀錄歲月的面容/張詠捷(攝影)台港電影中的原住民形象塑造──幾部影片的分析/迷走博物館及其對台灣原住民文化的製造/任海台灣原住民塑像的社會心理背景/傅仰止星火/陳映真山海評論「兼足天下之道在於明分」:八十三年度中央政府原住民預算的省思/高德義走出「運動場」和「舞台」的局限/林志興原住民文化運動的歷史位置/劉紹華詩拳與淚/溫奇退出/溫奇彌伊禮信的頭一天/阿道‧巴辣夫魚等待,飄出一朵微笑的雲/董恕明鬥魚撞上了女人中的女人/董恕明散文餘跡/陸雅林小說等待貓頭鷹的日子/拓拔斯‧塔瑪匹瑪黑潮の親子舟/夏曼‧藍波安劇本島上的人(上)/蔡逸君、劉宇均、夏曼‧藍波安、夏曼‧夫阿原合著山海文論原住民文學的困境──黃昏或黎明/孫大川找回聲音,握緊筆桿──兼記民間出版原住民作品情況/浦忠成山術海藝刀子的藝術/王煒昶原住民樂舞的內憂外患/林桂枝山海醫療原住民年看原住民健康困境/孔吉文部落史卑南族知本部落口傳歷史及神話故事(上)/曾建次歷史剪影歷史的影像、影像的歷史/海若山海兩岸民族新生現象的塑造──歌頌歌謠與生活評斷/謝世忠大陸有關台灣南島民族語言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曾思奇國際原壇藍色的群山/弗‧桑吉著、劉憲平譯日本國內的少數民族問題/久部良和子、阿基姆‧塔拉西著、劉憲平譯山海笑話爸爸是高山族/多多誰是山地人?/多多要我們很忙嗎?/多多山海日誌八十二年八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阿WU輯山海季節八十二年十月至八十三年一月/編輯部輯山海世界-《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序孫大川 原住民文學的逐漸茁壯,是民國七十年代以來,台灣文化界中一個重要卻不太為一般人所注意的新動向。它的重要性不只是因為它指出了一個以「山海」為背景的文學傳統,更重要的是:我們終於能看到原住民作者,嘗試以主體的身分,訴說自己族群的經驗,舒展鬱積百年的創造活力。原住民各個族群,正試圖以他們的文學和藝術的想像力,以他們厚實、質樸的生活智慧,從「山」上的石板屋,「海」裡的獨木舟,走向全世界。 對原住民而言,「山海」的象徵,不單是空間的,也是人性的。它一方面明確地指出了台灣「本土化」運動,向寶島山海空間格局的真實回歸;另一方面也凸顯了人類向「自然」回歸的人性要求。他不同於愈來愈矯情,愈來愈都市化、市場化的「台灣文學」,也不同於充滿政治意涵的所謂「台語文學」。長久以來,原住民卑微、苦難的經驗,使他們的文學筆觸、藝術造形以及文化反行省,更能觸及到生命的本質和人性的底層。 《山海文化》的創刊,就是預備為原住民搭建一個屬於自己的文化舞台;在這個舞台上,讓我們的同胞盡情揮灑自己的文學才華、藝術想像、文化創見以及獨特的政經觀點。 不過,要建構原住民的文化空間,不能單憑個人旺盛的創造活力,他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與自己民族得文化傳統銜接、交談;這種關係乃是辯證的,是一種既「返本」又「開新」的實踐歷程。基於這個了解,《山海文化》版面空間的配置,就必須兼顧傳統與創新的均衡發展。「部落史」、「歷史剪影」,神話和傳說、祭典與民間歌謠的記錄、採集、分析,以及傳統工藝、美術的研究、介紹,便構成了《山海文化》重要的組成部份。 當然,這些傳統的挖掘,其目的並不是為了「文化展覽」,更不是為了考古上憑弔的需要,它永遠有一個清楚的落點:即是厚植、深化原住民創造力的基礎,使我們的文化勞動,不但元氣淋漓,而且也能呈現祖先的面貌。 語言文字的問題,也是《山海文化》必須克服的難題。原住民過去沒有嚴格定義下的「書寫」系統,因此「雜誌」的呈現,對原住民各族原來的「言說」傳統,其實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通常我們可以嘗試兩種策略:或用漢文,或創製一套拼音文字來書寫。《山海文化》的立場,願意並同時鼓勵這兩種書寫策略;而且為尊重作者本身所習慣使用的拼音系統,我們不打算先釐訂一個統一的拼音文字,讓這個問題在更充分的實踐、嘗試之後,找到一個最具生命力的解決方式。 漢文書寫方面,在語彙、象徵、文法以及表達方式的運用上,我們亦將採取更具彈性的處理原則。因為,我們充分理解到原住民各族皆有其獨特的語言習慣和表達手法;容許作者自由發揮,不但可以展現原住民語言的特性,也可以考驗漢語容受異文化的可能邊界,豐富彼此的語言世界。 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走回頭路或自我封閉是不可能的,《山海文化》所欲拓展的世界,因而當然也是開放的。我們不僅希望原住民作者努力創作,更期待非原住民的朋友參與。只是為了讓我們的焦點集中,並凸顯原住民的觀點──這個觀點,往往是被主導社會漠視甚至扭曲的──我們希望非原住民作者能以和原住民相關的「題材」來創作,不論那是肯定的或是批判的,而具原住民「身分」identity的作者,則可以觸及任何的「題材」。這是《山海文化》本身性質的限制,其間實無意形成「我族中心主義」的妄念。 正因為如此,我們的視野並不希望被局限在台灣原住民身上。彼此甚至廣泛的第三世界少數民族的處境、經驗極其豐富的文化資產,都是我們關心、探討的主題。我們深深相信:一個僅僅以漢民族為中心的歷史敘述或文化論述,不僅不完備,甚至會窒息整個民族文化的生機;而以白人為中心所宰制的世界,也終將逼使人類枯槁而死。《山海文化》的創刊,因為具有了一個世界史得幅度! 「書寫」意謂著某種菁英化的傾向,因而,或許有人會質疑《山海文化》是否還能與部落保持緊密的關係?是否能真實反映部落的需要、情感?這的確是《山海文化》最大的陷阱,是它自始至終要去面對的挑戰。顯然《山海文化》的戰線或任務是兩面的;一方面它必須積極介入主導社會的各項文化議題和創造性活動;另一方面也必須敏銳地把握、捕捉迅速變化中的原住民部落社會。為了盡可能滿足這兩面的需要,我們將不斷加強對部落動態的報導,鼓勵更多在部落的同胞加入我們創作的行列。可以肯定的是: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光是質疑、批判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積極介入的勇氣和決心,需要實際參與的「行動」;讓我們共同決定《山海文化》的路線和品質。 就因於這個緣故,團結、合作便成為《山海文化》生命真正的原動力。如何捐棄族群矛盾、個人利益、政治路線等的糾纏,不但是對《山海文化》的考驗,也同樣考驗著我們全體原住民社會。《山海文化》的任務是要去「創造」一個舞台,而不是要去「佔有」它! 原住民當前的處境,以不容許我們繼續以斷裂的「點」、「線」形式來應付、搪塞,一時的苟且、短視,將無可避免地逼使我們重蹈十九世紀末平埔族消失的命運。文化的創造,固然無法讓我們看到立即的效果,但它卻可以穿透時空的限制,凝聚我們的智慧,獲得生生不息的生命。 「山」盟「海」誓,是我們跨越世紀末的唯一憑藉;它不是一個浪漫的情緒,而是一項責任,決定將原住民祖先的面容,一代一代傳遞在這原本屬於他們的島嶼上,成為永恆的記憶和永續不斷的創作源泉。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製作,所有內容均受智慧財產權及相關法律保護。
基本資訊
- 原始資料連結
- 資料來源
- 主題分類
- 建檔單位
- 作品語文中文
- 地圖
本網站使用Cookies收集資料用於量化統計與分析,以進行服務品質之改善。請點選"接受",若未做任何選擇,或將本視窗關閉,本站預設選擇拒絕。進一步Cookies資料之處理,請參閱本站之隱私權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