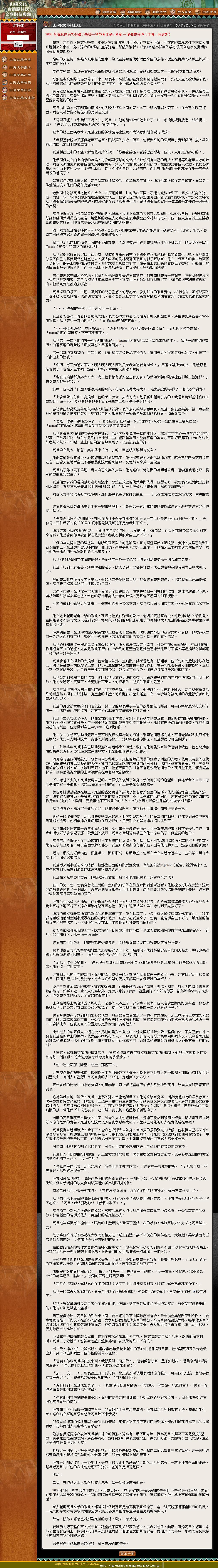跳到主要內容區塊
:::
山海文化 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
山海文化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資料檢索請輸入檢索字2003台灣原住民族短篇小說獎-得獎者作品/名單-漫長的等待(作者:陳康妮) 暗夜,瓦旦跳上達袞的野狼,兩個人瘦弱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夜幕的彼端,在夜晚的寒風陪伴下兩個人用身體相互依偎在一起;達袞的野狼在產業道路上緩緩的潛行,野狼125發出低聲的喘息慢慢穿過黑夜揭開兩個夜行者的面紗。 後座的瓦旦用一道強烈光束照向空中,燈光在路邊的樹群裡面來回的穿梭,試圖在樹叢的枝幹上找到一雙亮亮的眼睛。 從遠方望去,瓦旦手電筒的光束好像從漆黑的地底竄出,穿過幽黯的山林一直慢慢的往深山前進。 野狼在產業道路的盡頭停了下來,達袞拿下鑰匙把綁在野狼側邊的獵槍取下,先把瓦旦的槍遞給了他,瓦旦把戴在頭上的頭燈掛在腰上的小電池打開,小心的測試頭燈會不會發亮。 這時候被黑夜層層包圍的兩個泰雅族人,在頭燈的照射下身後陰暗的身影透著幾分滄桑,一件退伍帶回的褪色草綠服,束管的運動褲配上雨鞋,背著綠紅相間的塑膠背袋,背後一支有一點生鏽的土製獵槍,一雙歷經風霜粗糙的雙手。 瓦旦從口袋拿出了剛買的檳榔,他先咬去檳榔上面的蒂,拿了一顆給達袞,丟了一口在自己的嘴巴裡面,兩個人嚼著檳榔用低沈的語調在交談。 「馬索勒嘎!(準備好了嗎?)」瓦旦一口把的檳榔汁朝地上吐了一口,然後把檳榔放進口袋準備上山。「達袞今天來找你那個老黃說一隻要收多少。」 達袞的臉上面無表情,瓦旦從他的神情猜得出達袞不大滿意那個老黃的價錢。 「我聽巴彥說今天那個老黃不老實,跟部落的人收二佰五,他賣到平地的餐廳可以賣到伍佰一隻,早知道我們自己去山下的餐廳賣。」 瓦旦聽出巴彥的不滿,對著他冷冷的說:「你要賣給誰,賣給派出所嗎,傻瓜,人家是有辦法的。」 他們兩個人在山上抬槓的時候,每次都對價錢的高低斤斤計較很有自己的看法,可是等到老黃來收的時候,兩個人從頭到尾對那個開著跑車的姆幹(漢人)開的價錢都很阿莎力,熱情的請那個人喝酒,他們心裡想反正在山上有的是不用本錢的動物,晚上多打幾隻就可以賺回來,而且有門路銷出去也就不在乎一隻差幾百塊的差價了。 等達袞停好摩托車之後,瓦旦背著槍往路邊的一處草叢鑽了進去,達袞也隨後跟在瓦旦後面,向著另一條獵徑走去,他們的動作安靜熟練。 進到樹林之後瓦旦把槍拿在手上,四周是漆黑一片的幽暗王國,頭燈的光線指引了一條狹小明亮的道路,雨鞋一步一步沙沙的踩在堆滿枯葉的地上,穩健低沉的腳步聲讓周圍充滿了肅殺的氣氛,大部分的時間瓦旦的眼睛都隨著頭燈的光線,四處遊走在頭頂的樹枝中間,犀利的眼睛像雷達一樣準備鎖定任何一處光點的出現。 瓦旦慢慢在每一棵飛鼠喜歡棲息的樹木搜尋,從樹上嫩葉的咬痕可以透露出一些蛛絲馬跡,他豎起耳朵仔細聆聽樹葉間發出的聲音,用靈敏的嗅覺去分辨出空氣中散發出來特殊的氣味,他一個人獨自行走在陰森鬼魅的樹林裡面,隨時主宰著躲藏在樹葉後面的大眼睛。 四十歲的瓦旦在小時候yava(父親)告訴他,如果在黑暗中越恐懼害怕,越會被utux(邪靈)帶走,要堅定自己的意志才能變成一個優秀的泰雅族獵人。 黑暗中瓦旦的動作還是十分的小心跟謹慎,因為他知道不管他的經驗跟年紀多麼老到,他仍要遵守山上的gaga(祭儀)跟黑夜的叢林法則。 瓦旦在樹林裡面繞了快半個小時,整座樹林裡面只有地上的樹蛙跟他走動的腳步聲產生共鳴,瓦旦漸漸放慢了自己的腳步腰桿也挺直起來,廣大幽深的樹林間連個飛鼠的影子都沒有。他在一棵巨大的倒木前面停下了腳步,把手上的槍往背後擱著,仰起頭看著周圍的樹木,右手在上衣口袋裡面找出了香菸,糾結在一起的眉頭似乎更伸展不開,他坐在倒木上休息叼著煙,打火機的火光短暫而溫暖。 白色的煙霧在四周散開來,他豎起耳朵仔細聽著達袞的槍聲,樹林間靜的有一點詭異,沒有風聲也沒有一些平常熟悉叫聲,瓦旦心裡想這兩年是怎麼了,這個山上的動物越來越難打了,有時候還要翻過好幾座山,牠們究竟是都跑去哪裡。 瓦旦深深的吸了一口煙,滿腦子的胡思亂想,他想起有一次把打來的飛鼠賣給一家小吃店,正好部落的一個年輕人喜濫也在,他跟朋友在聊天,喜濫看見瓦旦拿著背袋的飛鼠跟老闆在算錢,就拉著他跟他抬槓起來。 「mama(長輩的尊稱)坐下來聊天一下嘛。」 瓦旦看著喜濫一直看他賣飛鼠的錢,他的心理知道喜濫恐怕沒有聊天那麼簡單,最怕聊到最後喜濫會叫他買單,瓦旦表明一滴酒也不沾。「喜濫mama家裡還有事。」 「mama不要那麼酷,請兩瓶嘛。」「沒有打幾隻,錢都要去還阿路(債)」瓦旦面有難色的說。「mama我跟你開玩笑,不要那麼緊張。」 瓦旦鬆了一口氣拍拍有一點酒醉的喜濫。「mama現在的飛鼠是不是越來越難打。」瓦旦一副嚇到的表情,拍著喜濫的肩膀說「那麼厲害的喜濫有研究。」 二十出頭的喜濫猛喝一口酒之後,他的態度好像告訴旁邊的人,這個天大的秘密只有他知道,他擦了一下鬍渣上的酒說。 「你們一定不知道對不對,嘿!嘿!嘿!因為只有我知道我有線報。」喜濫指著所有的人一副睡眼惺忪的樣子,看在瓦旦眼裡一點都不好笑,旁邊的人卻跟著起鬨。 「現在的飛鼠都有辦大哥大,晚上他們都有派安全士官把風,你們如果騎野狼帶槍他們馬上就通報。」在場的人聽完都笑了。 其中一個人說「什麼!那麼厲害的飛鼠,有站安全帶大哥大。」喜濫突然舉手做了一個開槍的動作。 「上次我磅的打到一隻飛鼠,他的手上有拿一支大哥大,是最新那種可以折的,我還有聽到基地台呼叫的聲音,還一直叫他。喂!喂!喂!安全飛鼠請回答,是不是有狀況。」 喜濫拿出行動電話學飛鼠嘰嘰的叫聲講行動,他的朋友笑得快要中風,瓦旦一張老臉哭笑不得,這是他聽過去打飛鼠最烏龍的笑話,現在的年輕人都喜歡把一些新名詞加到談話裡面,還很會吹牛。 「喜濫,你是不是喝太多了。」喜濫搭著瓦旦乾完一杯米酒之後,咚的一聲趴在桌上喃喃自語。「mama沒有騙你,我真的有看到那個飛鼠還有背值星帶。」 瓦旦看著喜濫喝醉的樣子不禁搖搖頭,部落有很多像他一樣的年輕人,在都市打拼了一段時間後又回到部落,平常靠打零工維生或是到山上捕獵一些山產貼補家用,也許喜濫的寓言故事剛好反應了山上的動物為什麼越來越少,年輕一輩上山打獵都百無禁忌了,也忘記長輩的話。 瓦旦坐在倒木上抽著。突然傳來「磅!」的一聲劃破了寧靜的夜空。 他向著槍聲來源望去,心裡想達袞終於開張了,他依循聲音的方向估計達袞現在跟自己距離有兩百公尺左右,正當瓦旦思索自己不要重疊到達袞的範圍時,又急促傳來第二聲槍聲。 瓦旦站了起來丟下香煙,看來自己高興的太早,他從達袞二槍之間的時間差來看,達袞應該是把那一隻幸運的飛鼠給放生了。 瓦旦抬頭安靜的看飛鼠有沒有飛過來,頭燈在茂密的樹葉中間找尋,他想起有一次達袞的死對頭巴彥特別消遣他,直接拿筷子去量他兩個眼睛的距離,又比一下旁邊瓦旦的眼睛,然後無奈的說。 兩個人的眼睛也沒有差很多啊,為什麼達袞每次都打到飛鼠——(巴彥故意拉長語氣接著說)旁邊的樹呢。 達袞看著巴彥笑得死去活來有一點懶得理他,可是巴彥一直用難聽的話去挑釁達袞,終於讓達袞忍不住有一點火大。 「巴彥你也好不到哪裡啦,部落裡面連小孩子都知道你的五支十字弓鋁箭還插在山上的一棵樹。」巴彥馬上不甘示弱的說「何必在乎過程最後飛鼠還不是被我打下來。」 達袞帶著一些輕蔑的笑容。「全世界只有你用七、八支箭去射一隻飛鼠,你以為那隻飛鼠是被你射下來的嗎,他是看到你每次都射在他旁邊,嚇到心臟麻痺自己掉下來。」 二個中年人從自己的爛槍法一路吵到互揭對方的性缺陷,爭的面紅耳赤血脈噴張,旁邊的人早已笑到抽筋倒在地上,瓦旦想起當兵時候的一個口號,榮譽是軍人的第二生命,不過在瓦旦眼裡眼前的兩個同學,嘴上的功夫比他們的槍法跟性能力厲害多了。 瓦旦回神聽著剛才達袞的槍聲,決定轉向另外一條獵徑,往更幽深的獵場一個人獨自走去。 瓦旦下切到一處溪谷,涉過短淺的溪水,遁入了另一處密林裡面,他心想在約定的時間內出現就可以了。 眼前的山勢並沒有較之前平坦,有的地方是陡峭的石壁,聽著達袞的槍聲遠了,他的腰帶上還滿是彈藥,瓦旦雙手握著槍決定在這裡試試手氣。 果然很快的,瓦旦在一棵大樹上面看見了閃光閃過,他安靜繞到一個有利的位置,迅速熟練蹲了下來,裝填彈藥然後高高舉起槍,當他的眼神跟亮光交會的時候,瓦旦毫不思索的扣下扳機。 火藥的煙硝化做強大的聲音,一個黑影從樹上飛落下來,瓦旦飛快向大樹底下奔去,他計算飛鼠落下位置。 他在地上發現奄奄一息的飛鼠,瓦旦把他放在背後的背袋,繼續往更裡面走去,他撥過雜亂的矮樹叢,在距離剛才不遠的地方又看到了第二隻飛鼠,眼前的飛鼠比起剛才的更顯碩大。瓦旦的槍聲又穿過樹葉向黑暗發出巨響。 待煙硝散去,瓦旦撥開四周樹叢在地上找尋落下的飛鼠,他抬頭向半空中茂密的枝幹尋找,他知道這方圓十公尺之內都有可能,果然在一棵樹枝上發現了滴著血的飛鼠,是一隻白面的飛鼠。 瓦旦心裡知道這一種飛鼠是保育類的飛鼠,漢人的法律規定不能打,可是在部落gaga裡面,在山上的動物哪裡有不打的道理,尤其是飛鼠不管在山上看到的是藍色還是綠色通通給他照打不誤,等毛燒掉之後都是一樣的顏色就是黑色。 瓦旦看著掛在樹上的大飛鼠,他拿槍去勾那一隻飛鼠,結果還是有一段距離,他不死心乾脆把槍放在地上,選了旁邊的一棵樹爬了上去,他小心翼翼的把身體靠在一根枝幹上,右手緊抓著旁邊較粗的樹枝,瓦旦一點一點移動身體,左手幾乎要抓到那隻飛鼠,就是差了幾公分,這已經是瓦旦身體的極限了。 瓦旦重新調整左右腳的位置,冒險的把腳放在更細的樹枝上,頭燈的光線來來回回在飛鼠跟自己腳下移動。他的身體張的更開了,手更延伸了出去,他輕易的一把抓住飛鼠的尾巴。 瓦旦正當得意的收回左腳的時候,腳下突然傳出啪的一聲,樹枝硬生生從枝幹上斷裂,瓦旦整個急速的往地面墜落,樹下正好連接一處垂直的山壁,他身體在石壁上碰撞,在一陣吵雜之後瓦旦的身體很快被四周的黑暗給吞噬。 瓦旦的身體被重重摔下山谷之後,另一處的達袞還是專注的找尋飛鼠的蹤跡,可是他突然感覺有人叫了他一下,他回頭什麼也沒有,達袞回過頭繼續在安靜的樹林裡走著。 瓦旦不知道昏迷了多久,他開始在痛覺中恢復了意識,他感覺從他的四肢、胸部好像在撕裂他的身體,他不斷的掙扎呻吟要起身,每一個小移動都痛的他幾乎受不了暈過去,他沒有辦法使喚他的身體,瓦旦知道自己傷的很重,他意識到自己yaqiume(碰到厄運)。 他一次一次想要移動身體讓自己可以爬行或翻身匍匐前進,離開這個厄運之地,可是最後都失敗只好躺在原地,他想用力叫喊達袞,胸部的劇痛讓他差一點連呼吸都沒辦法,瓦旦想肋骨應該也斷了。 在一片黑暗中瓦旦連自己扭曲變形的身體都看不清楚,現在的他可能只有等待達袞來救他,他也開始害怕如果達袞沒有來要怎麼脫離這個地方,他始終相信達袞一定會來。 四周暗的讓他胡思亂想,隨著時間分秒過去,瓦旦的瞳孔慢慢的適應了周圍的光線,他可以清楚的從樹縫中微弱的光線看見深藍色的天空,乳白色的雲朵讓他感覺到自己再移動,他的眼睛直直看著天空,突然想起教會牧師的話,有一次講到天國的樣子,他想天國的入口會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瓦旦並不是一個虔誠基督徒,他突然覺得悲憫的上帝絕對會在這個時候眷顧他。 不知道過了多久,瓦旦發現自己的左手慢慢的恢復了知覺,手指可以隱約碰觸到一個毛茸茸的東西,原來是剛才那一隻飛鼠,他的上臂還有一點酸麻,瓦旦還是試著活動左手。 整個身體還是癱瘓在地上,瓦旦的腦海痛苦的拼湊了整個意外發生的情形,他開始後悔自己愚蠢的決定,違犯獵人的禁忌,長輩曾經在他年輕的時候告誡他,不可以遠離自己的同伴,還有吊掛在懸崖旁邊的獵物是utux(鬼魂)的陷阱,要放棄牠不可以貪心的去拿,當你拿到的時候也是靈魂被帶走的時候。 瓦旦的貪心,應驗了長輩的詛咒,他痛得無法自己,他不斷的從懊悔中痛苦得不能自己。 經過一段漫長時間,瓦旦身體變得麻木起來,他開始豎起耳朵,聽著四周的動靜,他注意到很久沒有聽到達袞的槍聲,他相信達袞此刻應該在附近找他,只要耐心的等待達袞很快就到了。 瓦旦想起跟達袞這十幾年相處的情形,國中畢業一起跑過遠洋,在一望無際的海上日夜不停的工作,海水和淚水好幾次模糊了那一段青澀的歲月,瓦旦才發現達袞早已在他生命中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 瓦旦用左手慢慢的在口袋裡面找出了香煙跟打火機,他一點一點的把香煙往嘴裡送,再把打火機點著,他的左手是全身唯一可以自由移動的部分,瓦旦叼著煙卻沒有辦法吸,因為他的肋骨差一點穿破他的肺臟。 煙的一點火光好像給他一點溫暖,一點點明亮一點點希望,他用左手在身體旁邊堆起一些枯葉,用打火機升了一個小火堆取暖。 瓦旦等火漸漸旺起來的時候,把那隻白面的飛鼠丟進火堆,算是把象徵yagiume(厄運)給消除掉。也許達袞看到火光聞到飛鼠的味道就會很快趕過來。 瓦旦在火光中靜靜等待,他始終沒有放棄一點希望他知道達袞一定會趕來救他。 在山的另一邊,達袞背著晚上射的二隻飛鼠飛快的在約定時間到獵寮裡面,他把槍收好放在旁邊,達袞突然覺得奇怪看了一下四周,通常這個時候都是瓦旦比他先到,然後他會升起火堆把飛鼠的毛去掉,達袞在一旁看著瓦旦享受美味的腸子。 達袞坐在木頭上面抽煙,他心裡猜想今天晚上瓦旦到底會射到幾隻,他折著乾柴準備起火心想瓦旦今天晚上可能欲罷不能了,達袞開始抱怨瓦旦害他一個人在獵寮枯等,早知道射到天亮就好了。 達袞的煙沒有離開過嘴巴飛鼠的毛也都燒完了,他在枯等了快一個小時之後情緒開始起了變化,一種不祥的預感油然而生漸漸籠罩在他的心頭,他有一點擔心起瓦旦來了,達袞一直告訴自己不可能,以瓦旦的經驗跟技術都在他之上,這麼多年只要在山上出問題瓦旦都會趕來解救他。 看著眼前陰森黑暗的山林,達袞站起來打開頭燈走向外面,他試著面對漆黑的樹林喊瓦旦的名字,「瓦旦,你在哪裡。」他一遍一遍喊著。 達袞開始不安起來,他的語氣也變得焦急,緊張短促的音波向空曠的樹林縫隙奔去。 達袞漫無目的走著突然被懸空的藤蔓給絆了一下差一點摔倒,他站穩腳步後用向四周照去,黑暗讓失蹤的瓦旦好像變成了幽靈。「瓦旦,不要開玩笑了,趕快出來。」 「瓦旦,你不要嚇我。」達袞沒有聽到瓦旦的回應急忙奔回野狼那裡,跳上野狼用最快的速度奔回部落,他知道一定出事了。 達袞到瓦旦家用力的敲門,瓦旦的太太伊醬一聽,嚇得手腳發軟差一點昏了過去,達袞找了瓦旦的弟弟哈用,兩個人跑去找村長比令,比令立刻帶著他們找了部落十多個青壯的年輕人。 凌晨三點原本寧靜的部落,變得騷動起來,在泰雅族的gaga(傳統、祭儀)裡面,族人失蹤是很嚴重撼動部落的一件事,老一輩的人認為部落一定有人觸犯了gaga,祖靈要降下不好的懲罰,部落廣場聚集了很多人,現場的氣氛也陷入了沉重的陰霾當中。 比令在馬路上集合清點了所有人,全部的人跳上了二部貨車,達袞一個人在前面騎著野狼帶路,他心裡祈禱瓦旦可能是忘了時間或是頭燈壞掉了,搞不好是整件事是烏龍一場人已經路邊等了。 達袞飛快的速度趕到他們出發的地方,眼前的景象更加深了一種不祥的預感,瓦旦並沒有出現在族人的面前,族人陸陸續續跳下車,比令問達袞今天晚上打獵的範圍,達袞指著黑暗的山脈把自己去過的地方一五一十告訴比令,他說瓦旦的位置應該是靠西面山麓的地方。 比令把人分成五個人一組之後,迅速的隱入草叢之中,燈光與呼喊聲交錯在整個山林,不久巴彥在地上發現瓦旦在倒木上的煙蒂,他大聲叫喚所有的人,一時之間所有的人的燈光集中向那裡奔去,比令看著瓦旦雨鞋踏過的痕跡,他小心的從地上植物推斷瓦旦行進的方向,雨鞋踏過的草葉方向讓比令心裡有種不祥的預感。 「達袞,你有聽到瓦旦的槍聲嗎?」達袞搖搖頭不確定有沒有聽到瓦旦的槍聲,他努力回想晚上打飛鼠的每一個細節。比令皺著眉頭朝著瓦旦的腳蹤看去。 「他一定去司那(斷壁、懸崖)那裡了。」 大家突然臉色凝重起來,那個地方平常白天就不太好走,晚上更不會有人想去那裡,那裡山勢陡峭之外石壁又多,每個人心裡想如果瓦旦真的去了那裡一定遇到了大麻煩。 五十多歲的比令口中念念有詞,他用泰雅古語祈求祖靈能保佑族人平安找到瓦旦,無論多麼艱難都要找到他。 這時候躺在地上等待的瓦旦,虛弱的連左手也懶得動了,他從來沒有覺得一個夜晚是如此的漫長寂寞,他平靜的看待自己生命,他試著用回想這一生中發生過的事來度過這個又黑又痛的長夜,最讓他掛心的還是家裡的人,尤其是兩個國小的孩子,出門前看到他們熟睡在他們yaya(媽媽)身邊的樣子,還答應他們用賣飛鼠的錢,帶他們下山去逛夜市、吃牛排、買玩具,這些恐怕要泡湯了。 漸漸的瓦旦發現天空慢慢的白了,身旁的火光也逐漸黯淡,經過了長夜到黎明的轉變,期待對瓦旦來說好像沒有很大的意義,瓦旦心想達袞也許回到家呼呼大睡了,世界上可能沒有人在意他躺在這裡。 瓦旦覺得身體開始冷的受不了,全身也漸漸失去知覺,當四周的景物變亮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撐了好久變得好累好累,好想閉上眼睛好好睡覺,可是他知道只要閉上眼睛,可能再也無法見到兩個可愛的孩子,幾次眼皮像千斤的重量拉下來,他都告訴自己不可以睡,他漸漸沒有辦法用意志力來支撐自己。 恍惚間,聽見有人叫了他的名字,可是瓦旦累的不想去回答,從頭頂的聲音越來越清楚。 直到有人不斷的拍打他的臉,瓦旦奮力的睜開眼睛,他蒼白虛弱的臉看著前方,比令發現瓦旦的眼神呆滯還不斷喃喃自語。「是上帝嗎?」 「是原住民的上帝,瓦旦起來了,我是比令來帶你回家。」達袞在一旁焦急的說。「瓦旦搞什麼,不要嚇我,你到底怎麼樣了。」 達袞握著瓦旦的手,看著他身上的傷自責又難過。全部的人都小心翼翼的攀下石壁陸續下來,比令趕快派二個身手矯健的族人奔回部落通知派出所叫救護車。 同學巴彥也在一旁安慰瓦旦。「瓦旦怎麼會這樣,每次你都叫別人要小心。你自己都沒有小心。」 瓦旦躺在地上虛弱的看著圍著他的族人,眼淚忍不住的從黝黑的臉龐流下,達袞擦著他的眼淚自己也哭了起來。「瓦旦,哈大那散啦!(我們回家了)。」 瓦旦喝了一點水之後仍然很虛弱。部落的年輕人很快利用樹枝黃藤做了一個擔架,比令看著瓦旦的傷勢,臉色凝重的告訴其他人,要盡快的送瓦旦出去。 瓦旦被牢牢固定在擔架上,眼前的山壁讓族人發揮了團結一心的精神,輪流用接力的方式把瓦旦接上去。 花了半個小時好不容易在大家同心協力之下送上石壁,接下來茂密的樹林也是一大難題,雖然前面有五六個族人在開路,可是在經過較密實樹林的時候。 在前面抬擔架的樓信與吾麥些在時間的壓力下,擔架都會不小心勾到樹枝不顧一切粗魯的把擔架硬扯,好幾次瓦旦差一點從擔架上摔下來,臉色蒼白的瓦旦都痛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吾麥些在後面看見瓦旦的眼淚笑著說:「瓦旦,不要感動的一直哭嘛,我會不好意思。」瓦旦已經痛的不知道要說什麼,他想以樓信跟吾麥些的抬法,回到家恐怕也不行了。 他虛弱的跟前面的樓信說。「樓信,拜託一下,帶路看一下路嘛,不要一直衝,慢慢來,我不會急,卡住的時候溫柔一點嘛。」後面的吾麥些聽到又開口了。 「瓦旦你很囉唆,你以為你在坐飛機嗎?還有空中小姐按摩服務喔。沒有叫你自己走就不錯了。」 瓦旦一聽完吾麥些說的話,看著自己斷了兩截L型的腳,還是閉上嘴咬著牙,享受著原住民VIP的待遇了。 整路上雖然顛簸可是瓦旦感受了族人的細心照顧,還有吾麥些原住民式的冷笑話,雖然受了很嚴重的傷,他的心卻是滿滿的溫暖。 到了產業道路,瓦旦被抬到貨車上面,貨車迅速的下山與救護車會合,貨車從產業道路下到公路,小貨車急速的往山下開去,在狹小的公路,大家遠遠就聽到救護車的警笛,小貨車停在路邊等待,結果救護車的駕駛卻急速的從小貨車旁邊呼嘯而過,在旁邊揮手的比令當場傻眼,吾麥些更是氣得從車上拿出瓦旦的槍,要把救護車的輪胎射破。 小貨車只好轉頭追著救護車,追到了部落救護車才停下來。達袞看著瓦旦蒼白的臉,難過的掉下眼淚,瓦旦上了救護車,警笛聲迴盪在整個部落山谷飛快的往山下奔去。 第二天,達袞被叫去派出所。達袞響起昨天晚上發生的事心中還是很難平復,他低著頭沮喪的走進派出所,到了派出所裡面一個年輕的警員叫住他。 「達袞,你跟瓦旦搞什麼東西,我很難對上面交代。」達袞低著頭有一些不知所措。警員拿出紙筆要問筆錄。「昨天你們到山上做什麼,老實講不然罪很重!」 「去……去……。」達袞臉上有一點猶豫,他想到如果被關家裡就沒有收入,可是他又想邊一套故事就支支吾吾了半天,警員抬起頭不耐煩的說。「打飛鼠對不對。」 「沒有打到,瓦旦就出事了。」「真的沒有打到飛鼠嗎,不要騙我,老實講不然罪很重!」達袞一直搖搖頭看著那個趾高氣昂的警員。 「達袞那個打飛鼠的事我不寫,瓦旦的傷是怎麼用到的,我要寫記錄檢察官要看。」那個警員要達袞描述瓦旦意外的情形。 達袞想了很久嘴裡一直喃喃自語,警員乾脆叫達袞用表演的,達袞說瓦旦的胸部有骨折,腳跟右手也有,達袞站在原地用憑空想像瓦旦摔下來情況。 那個警員還真的根據達袞的表演來作筆錄,兩個人還不是停下來研究受傷的部位判斷瓦旦摔下來的先後順序,彷彿兩個人是現場的目擊者。 最後警員還要達袞表演瓦旦躺在地上的情形,達袞有一點不願意演,因為瓦旦的腳斷了兩截變成L型的,這是難度很高的表演,最後警員有一點半強迫叫達袞躺在地上,達袞只好很用力的硬ㄠ自己的腳,主管經過的時候看得哈哈大笑。 折騰了一個早上,好不容易那個把瓦旦的意外差點寫成武俠小說的二佰五警員完成了筆錄。還一直叫達袞要稱讚他的筆錄很完美把他的罪弄很輕,然後在筆錄上簽名蓋章。 達袞走出部落這間小丑派出所,天空下起大雨他低著頭往下部落瓦旦的家去,一路上達袞落寞的走著,越靠近瓦旦的家他的心就越激動不知道臉上劃過的是淚還是雨。 後記: 幸福,有時候對山上部落的族人來說,是一個遙遠奢求的夢。 2003年5月,真實世界中的瓦旦(我的表哥),並沒有在那一夜漫長的等待中,等待到一線生機,達袞在發現他冰冷身體的時候,半開的眼睛彷彿痛苦等待著好友的到來,達袞癱軟的坐在地上不斷懊悔的喃喃自語。 有人發現瓦旦左手的飛鼠,部落很快傳說瓦旦是被那隻飛鼠帶走了,老一輩更說那是邪靈附身的飛鼠,一時之間穿鑿附會許多禁忌的話題,族人都謙卑相信是主宰者在懲罰警惕族人。 待告一段落,部落也特別為瓦旦的意外,殺了一頭豬消災。 我靜靜的想了整件事,突然有一種全然不同別於部落的想法,以我對善良、幽默、風趣瓦旦的認識,意外發生的那個晚上,也許他只有單純想抓住眼前一個原住民簡單的祝福,兩個孩子的學費,家裡的開銷或是全家到夜市吃牛排的承諾。 只是都逃不過原住民的宿命,對幸福漫長的等待。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製作,所有內容均受智慧財產權及相關法律保護。
基本資訊
- 原始資料連結
- 資料來源
- 主題分類
- 建檔單位
- 作品語文中文
- 地圖
本網站使用Cookies收集資料用於量化統計與分析,以進行服務品質之改善。請點選"接受",若未做任何選擇,或將本視窗關閉,本站預設選擇拒絕。進一步Cookies資料之處理,請參閱本站之隱私權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