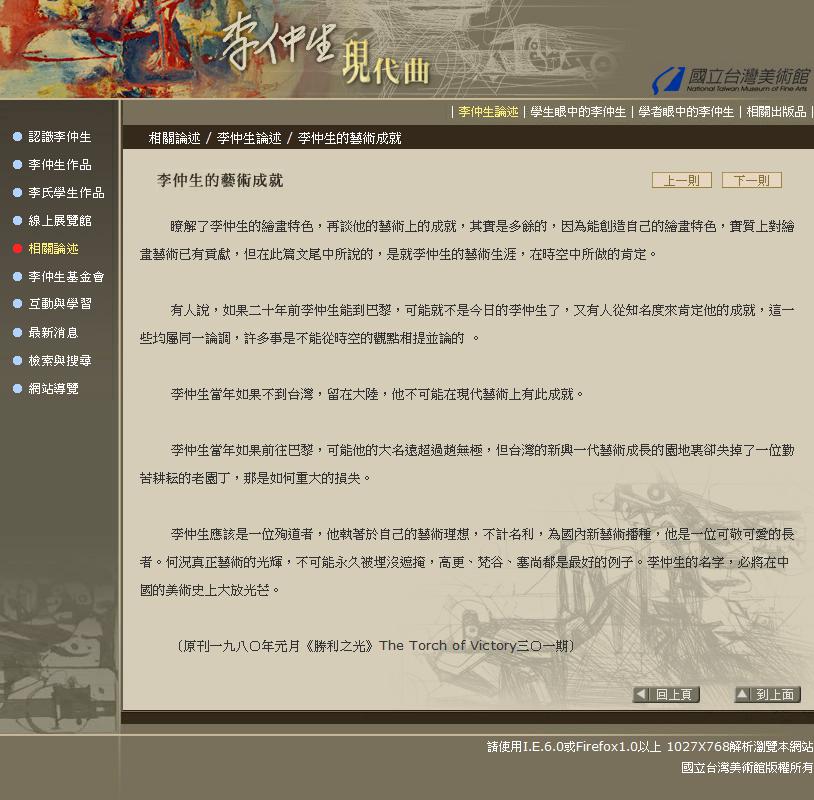跳到主要內容區塊
:::
相關論述&李仲生論述&「畫因」淺說李仲生
「畫因」淺說李仲生當我們考慮到藝術現象時,不能完全否定了自然,不過在此場合的所謂自然,不單是自然界所有的東西。這是指環繞著藝術家的週圍的自然,即加上所謂「環境」(Milieu)者而言。這不但從藝術現象的創造立場如此,就是批評的立場亦莫不皆然。特爾泰說得好,凡是各種精神狀態,只要惹起各種刺激,才可以使吾人理解,設無此等關係,則諸激情將無由表象云。在作畫活動說來,這事與為繪畫最重要根基的所謂「畫因」(Motif)者結合。在我們的作畫活動上,若除去了自然,則這種畫必然陷於純粹的內部感覺,無所謂表現的美的感情可言了。然我們在這裏的所謂自然,並不能與自然科學者所想像的所謂外界者等量齊觀。心理學者常對我們感覺上的某種特定客觀採用「刺激」這句話,這在心理學上是非常適當的一句話。藝術對於這「刺激」,一般地叫「畫因」,但藝術上的所謂「畫因」,究與心理學者的所謂刺激完全不同。心理學者的刺激,不過是感覺上的一種外界的事物而已,和藝術家的靈魂並無任何接觸,這在自然科學方面的情形,也大都如此。然就藝術說,因為藝術家的靈魂所描畫的意念,往往注意看那有藝術角度的事物。繪畫的基本根底就是「看」這件事。然所謂「看」,應如威爾菲林氏所云,那是要看那應看的東西,誠如此,其中便會發生各樣不同的藝術家的藝術的角度。藝術家看物時,為把物理的自然的形象,還原於藝術的形象,只要就如何以藝術家的眼去看的意念方向,便能由自然現象,還原於藝術形象了。換言之,就是以藝術的角度去看一切事物。所謂以藝術的角度去看一切事物,亦可以說就是對自然的一種否定作用吧。藝術家們在企圖著從藝術的角度向自然挑戰。在此場合,為藝術家們的靈魂所選取的形象可稱為「畫因」。故我們對「畫因」,似可稱為「自然物」(Nature-Object)。畫家們由其所謂「看」的感受性,而在其心目中選擇自然界中某一種美的東西時,我們往往指其選擇的形象為「畫因」。由此說來,在藝術上的所謂畫因者,乃是為藝術意慾所要求的自然形象,亦未嘗不可視為是一種刺激,然這並不能如心理學者所說的一切的事物具可成為藝術的刺激。藝術的刺激應該常與藝術家的藝術之魂相結合。亦即是為藝術家的意念所要求的自然形象。因之,所謂「自然物」就非得因藝術的要求而產生而規定的一種對象不可。某種自然物之為被規定了的對象,即為一種特殊化,他方面亦可說是對自然的藝術的還原。如我們個人的存在乃對他人即對社會而言一般,我們人的存在,亦可說是對外界即自然來說。在藝術上的所謂自然,再進一步說,即在繪畫上的所謂「自然物」,應該是由外界即自然,與內界即藝術心的接觸所產生的特殊的東西。畫家訴之於自己的感受性選擇自然界的某種美麗的部分於其心目中。其心目中所選擇的自然的某部分,乃對自然的一種壓迫,亦即對自然的否定作用。如果借利蒲斯的話,這叫「美的否定」。由於畫家們以美的否定作用,加之於自然,因而獲致高次的美的自然物。以藝術家的感受性及其藝術的創造力,這是可能的事。我們指此獲致的美的自然物為畫因。這裏所謂「自然物」,不是單純的自然物,那是由藝術家的感受性和創造力,把它放置於特殊的藝術形象或藝術的秩序裏面去的東西。如果再詳細地說,就是要捨棄自然所有的複雜的部分,去除其缺乏美的效果的東西,亦即是為得到藝術的效果而把它純粹化而集中統一起來。在一般人看來,所謂自然,恐怕只有把物的狀態原原本本地再現出來就算了吧。然作畫活動上的「畫因」是經過美的還原的,它不是自然的原來的物質,它是為畫心目中所選擇的一種沒有肉體的現象,那已經是一種美的還原。而必須逐漸使其集中於繪畫的效果,換置於藝術的秩序,然後才能為繪畫的Motif。故在藝術的立場,不但不容許有像自然科學般的精密的自然主義,抑且為不可能的事。從此點看來,我們視「畫因」為「自然對象」,毋寧欠缺妥當,如果以「自然對象」,加以真正的藝術性的解釋,不消說就是繪畫對象,當然就是「畫面對象」(Tableau-Object)了。近來此「畫面對象」一語,已漸為人們所使用在純粹繪畫方面,毋寧說是當然的事。「自然對象」一語,雖為部分人所採用,然如果我們解釋純粹繪畫,則這句話的文字內容,顯然不能傳達原有的意義,只要「畫因」與自然界的對象不同,而由畫家的感受性及其創造力所把握的東西,顯然是由所謂畫面者出發無疑。所謂繪畫的對象,至少都是繪畫性的東西,其具體的存在為畫面。所有繪畫上一切的思索與問題,都非從畫面考慮而解決之不可。故「畫因」亦為作畫過程的根基,自不能把畫面置之度外。雖則畫家每由其敏銳的感受性與創造力而切取了自然界的某種美的現象,或者由畫家的心所選擇的東西,總之,這畫家的心所選擇的東西,是要在畫面上具體化起來。畫家的心可以說就是一幅畫面。那裡畫家的心所選擇的畫因,便是在畫面上感到的選擇的好對象。所以所謂「畫因」,如果把由畫家的心所選擇的自然形象的想法再現實的說來,那就以此為對畫面上所感受的東西的一種把握較為妥當。由這畫面所獲致的自然形象,稱之為「自然對象」。這正如前面說過的,因為它是在畫面上所吸收的和感受的形態,故嚴密地說,那非得是「畫面對象」不可。只要是純粹的繪畫,那為繪畫底動機的「畫因」,必為「畫面對象」無疑。把「畫面」(Tableau)一語與「自然」(Nature)比較,顯然「畫面」一語,遠較「自然」一語使吾人有藝術的秩序之感而可以充分想像到美的還原這一回事。倘若以「畫面對象」為抽象的東西,那是錯的。蓋「畫面對象」這句話,並不包含任何抽象的意義,只意味著一切應從藝術的秩序、繪畫的立場及所謂畫面為根據出發。所以所謂「畫面對象」乃為朝著如何使畫面有著繪畫的效果的目標活動,而作為畫面對象,就必然要把握著「畫因」了。我們日常在客廳裏看到的中國畫,對於它的「畫因」並無奇怪之感。但構成中國畫「畫因」的山水人物,決不完全與我們眼簾相接觸的自然完全相同。那是為畫家的意念所要求,為中國畫的畫面所要求,亦即是為畫面對象所吸收的畫因而已。即在那裏增殖一種所謂藝術上的自然,高度的美的形象。這為畫面對象所要求的形象,就是「畫因」,而這「畫因」,在某種意味之下,就必定有形象。(原刊一九五二年八月《技與藝》月刊一卷二期,臺灣)
基本資訊
- 原始資料連結
- 資料來源
- 主題分類
- 建檔單位
- 地圖
本網站使用Cookies收集資料用於量化統計與分析,以進行服務品質之改善。請點選"接受",若未做任何選擇,或將本視窗關閉,本站預設選擇拒絕。進一步Cookies資料之處理,請參閱本站之隱私權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