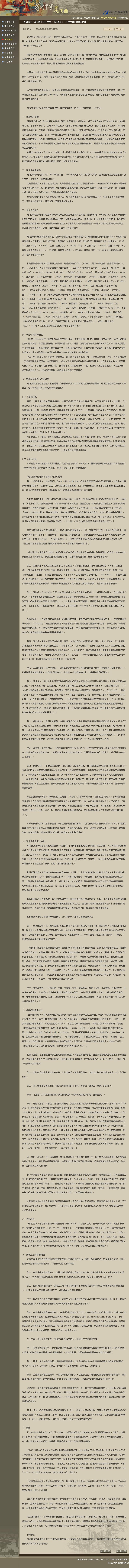跳到主要內容區塊
:::
相關論述&學者眼中的李仲生&「謝東山」-台灣美術中的李仲生主義
「謝東山」-台灣美術中的李仲生主義摘要在中國美術現代化過程中,畫家兼評論家李仲生把一生的教學願望,寄託在新一代的藝術家身上,誠然多過於任何他同時代的人。為了這樣的理想,李氏畢生不辭辛勞,努力栽培年輕藝術家,至死不渝。早期他所傳授的觀念帶有民族主義精神,以西方形式融合東方內容,並出現在東方畫會與50年代教誨的學生群。晚期的觀念則是徹底的現代主義與前衛主義,接受這種觀念的多為李氏後期的學生。在批評意識型態光譜上,他的學生實質上是從地方主義到國際主義皆有。李仲生死後,隨著藝術全球化之來臨,以不斷創新為根基的現代主義意識已逐漸受到質疑,代之而起的是以多元主義為中心思想的後現代創作意識。如果說,現代主義是對學院藝術的反叛,而前衛主義是以整個社會為敵,多元主義則是對現代主義的叛逆,對社會的合理妥協。就李仲生生前一貫的主張而言,這種不斷地對於成規的的反抗精神,正符合了他的畢生主張。從他所教導的學生群之各項轉變,正可以看到李氏精神的傳承。在李氏精神的傳承下,半個世紀以來已逐漸形成某種在台灣美術史上極為獨特的李仲生主義,它啟動了某種信仰與實踐方向,並在其死後日漸擴大其影響力。在台灣美術現代化過程中,畫家兼評論家李仲生一生透過教學方式,把他認為正確的現代藝術精神傳授給年輕的一代之餘,他的創作美學不但在自身的作品實現,也在其學生群中得到複製。雖然在批評意識形態光譜上,他的學生群並不完全一致,但多數學生的美學思想正逐漸形成某種可以稱之為「李仲生主義」的審美理想與審美價值觀。然而這種李仲生式的創作形式,在藝術收受上,長期以來並未受到重視。本文撰述目的在於從李仲生與其學生的創作理念中,探討「李仲生主義」的思想內涵與其面對的問題,根據的資料主要來自李仲生的著作,以及李氏學生2005年的創作理念(批評意識形態)自述,後者包括吳昊(1951)、金藩(1951)、夏陽(1951)、蕭勤(1951)、霍剛(1951)、朱為白(1952)、焦士太(1953)、蕭明賢(1953)、劉芙美(1954)、江漢東(1955)、鐘俊雄(1957)、梁奕焚(1958)、許輝煌(1958)、黃潤色(1960)、施淑(1962)、詹學富(1965)、朱麗麗(1968)、程武昌(1969)、黃步青(1969)、吳梅嵩(1973)、許雨仁(1973)、王慶成(1974)、李錦繡(1974)、林鴻銘(1974)、黃位政(1974)、陳孟岠(1976)、陳聖頌(1976)、黃銘宗(1976)、曲德華(1977)、張道燦(1977)、李杉峰(1978)、鄭瓊銘(1979)、原來(1980)、陳威宏(1980)、陳珠櫻(1983)、程菊瑛(1983)等36人的自述(以上按實際入李仲生門下的年份排序)。就人數來說,上述名單並未涵蓋所有李仲生的學生,但以取樣的標準來說,這36人已包含了李氏生前各時期的學生,因此,分析後的結果應與事實不致於有太大的出入。李仲生的「現代繪畫畫室」學生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臺北時期主要有吳昊(1951)、金藩(1951)、夏陽(1951)、蕭勤(1951)、霍剛(1951)、朱為白(1952)、焦士太(1953)、蕭明賢(1953)、劉芙美(1954)、江漢東(1955)等人,年代在1951與1955之間。1955年,李仲生離開臺北到員林家職,兩年後到彰化女中任教。彰化時期的正式學生始於鐘俊雄、梁奕焚、陳文夫。若按年齡排序,最年長的為朱為白與金藩,兩人俱出生於1926年。最年輕的是陳威宏,出生於1965年。在最年長的與最年輕的之間,時間跨越40年之遠。教學年代從1951年到1984年,時間長達33年,若扣除員林時期(2年)未曾招收學生,至少也有31年,幾乎等於一個大學教授的教學生涯。一、李仲生的藝術觀每一個從事藝術創作的人都有其自認的藝術價值觀,李仲生也不例外。李仲生的藝術價值觀直接影響了他的學生,這一點從其學生的創作自述俯拾皆是。因此,探討李仲生的藝術價值觀,對理解其學生群的批評意識形態顯然十分重要。李仲生曾說,他的作品是非主題性的、非敘述性的、非文學性的、非眼所見的心象世界、是暗示性的技巧表現、是感性的、是有機的,且富於神祕的生命現象。對此,李仲生曾加以說明:「繪畫本來就是視覺語言,又稱為繪畫語言,更有稱為國際語言的。繪畫語言或視覺語言,尤其是現代繪畫語言,已發展到一定要說明一個肉眼所見的現象世界時,也不一定要有條理地去敘述一件事;而毋寧更需要暗示或者象徵一個肉眼所看不到的心象世界了。」究其實際目標而言,李仲生的繪畫是以抽象的形式,再現其個人的直覺,性質與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繪畫相近,這裡面隱含著他個人的藝術價值觀。「藝術價值觀」一詞或許有點過於抽象,因為它好像無所不包,但若從另一種提問來說明,意義便清晰可見;那就是,什麼才是「好藝術」,或者更簡單的說法,什麼才是真正的「藝術」。李仲生心目中的好藝術或理想的藝術,必要具備哪些條件?以下我們將從藝術的再現問題來探索,並試圖從中找尋答案。(一)理想的藝術藝術再現問題的四邊形示意圖藝術的再現問題涉及藝術價值觀,並決定了一個藝術家的創作意識形態。當藝術的「再現」(representations)被「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時,人們總是圍繞著四個重大經驗軸線,對一些反覆出現的論題進行思考與闡釋。此經驗軸線分別連繫著四種關係,即「再現與自我慾望」、「再現與實體現象」、「再現與符號營造」、「再現與理想的藝術」四則之間的關係。自我、實體、符號、理想等四則概念便是現代人在藝術談論上的焦點,而且也是藝術再現此問題上,人們可透過經驗可觸及的。此四概念所形成的經驗結構,可說是構成人們藝術思考上知覺完形,在此基礎上,藝術家得以建構其獨特的藝術價值系統。在此,構成藝術「問題化」的四個重大經驗軸線中,其所關注的問題如下:一、「自我慾望」指的是創作者的意圖,亦即,他想要表現什麼?二、「實體現象」指的是創作者擬欲再現的素材與對象。藝術家總是針對某種他所熟悉的實體界現象,提出他對此現象的認知、推論、想像、批判。實體界包含自然與人為環境,若從空間上來講,又可分為個人、社會、國家、世界,從空間上來講,則可分為過去、當下與未來。三、「符號營造」包含構成藝術的題材(subject-matter)、內容(contents)、形式(forms)等。由此所組成的東西便是意象(imagery),它不是實體界本身,而是實體界的「摹本」,或者說「符號」(實體與意象其間的差異正如真實的一朵花與畫面上的一朵花)。藝術家唯有透過意象的營造,藝術的存在才成為可能的社會實踐活動。四、最後,在任何一個文化裡,藝術實踐總預存著某種或多種的指導原則,支配著生產者與收受者之間的認同,這種認同觀點,就經驗而言,通常並非可以科學地驗證的觀點,而更像是一個文化的共同理想,甚至是共同的想像。這便是「理想的藝術」(idealarts)的問題。正因為它在本質上屬於一個文化的共同理想或共同想像,「理想的藝術」因而在每個文化裡,其存在的形式更像是先驗的。造成這種事實的,無疑的,是某組審美理想,或政治的意識形態。在現代社會中,藝術家從自我的慾望出發,對實體世界進行感覺、知覺、認知、體會,而後使用其所能掌握的藝術技法,包括常規的或創新的,營造他所「想望的」意象世界。而在營造個人的意象之際,藝術家總是自覺地或無意識地遵守著被當代視為「理想」的審美理想。在藝術再現問題的四個重大經驗軸線,或者說四邊形中,自我慾望、實體現象、意象等三者所構成的三角形中,自我與實體形成一組對角線關係,它代表藝術創作者與外在世界的對應關係。連結這兩者的為意象世界,它是想像世界之具體化-由現實的題材、生活的內容、藝術的形式所構成。在符號(意象)的對面,亦即在它的對角線之一端,存在著理想的藝術。後者時刻閃爍著它的光芒,它是操控藝術生產與收受的無形力量之根源,但其形態卻總是隨著時間在改變而難以確切地被描述。在由「自我-實體-符號」與「自我-實體-理想」所組成的兩者間,一個文化中的藝術,恆能展開其所能開創的世界。(但也可以說,此四邊形的內涵,限制住一個文化在藝術再現事業上所能展開的範圍。亦即,每個文化在某個特定時期,總存在著它的頂和底,可能與不可能。決定它的,不是別的,正是藝術再現思考上,自我、實體、意象與理想四者在當時可能延展的範圍。)(二)形式軸就形式來說,在「符號」與「理想的藝術」之間,存在著無數的可變數(variations),存在於此軸線上的可變數從「形式即內容」(formascontent)的抽象藝術,到形式支撐內容的寫實藝術,再到無形式、只有內容(通常是文字)的觀念藝術,其間的變數無可盡數。在此,可變數具有兩種性質。第一,就相似性而言,在符號-理想線軸上,其可變數之間的關係並非斷裂,並非現代主義藝術家經常宣稱的絕然不同;在鄰近的兩個變數之間,它們的關係其實是連續的,是個別性的變數,存在著某種血緣關係。第二,就對立性而言,越是靠近符號這一端者,其物質性越高,推論性與想像性越少;反之,凡是越接近理想這一端者,物質性越低,但推論性或想像性越高。處於兩極中間的是物質與精神的結合物,而從歷史發展事實來看,它便是各式各樣,以模擬現實世界為目的寫實藝術。根據葛林柏格(ClementGreenberg)的說法,西方繪畫史的發展便是從中軸線出發,朝向符號這一端在前進,透過馬內、塞尚、馬蒂斯、畢卡索、波洛克,最後在後繪畫性藝術家筆下,走到繪畫藝術的最後一章。相反,黑格爾看到的是藝術史則是朝著相反的方向,逐步邁向哲學之路,而且最終將被哲學所取代。根據李仲生的說法,西方繪畫史的發展接近葛林柏格式的史觀,亦即,從幻象藝術中解放出來,走向媒材自身。至於最後會否走向後繪畫性藝術,李仲生並未曾明白表示過。但從他的評論中可以明確看出,藝術的最終命運是無法預測的。在「符號-理想」此一軸線上,李仲生傾向於相信符號只是為理想服務,但符號本身絕不應只當成隱形的、製造幻影的工具。因為他相信,現代藝術是反自然主義、反敘事性的。從後期印象派興起以後,現代藝術不再忠實描繪外在世界,這是因為現代藝術已放棄再現外在世界的企圖,如此一來,現代藝術必然會遠離敘事性的功能,「即使一定要說明一個肉眼所見的現象世界時,也不一定有條理地去敘述一件事;而毋寧更需要暗示或者象徵一個肉眼所看到的心象世界了。」正是在這樣的理念堅持下,繪畫不可能是具象的,或任何帶有說明性的功能。(三)內容軸但是在藝術再現過程中,徒有形式當然不可能達成再現的任務。在多數情形下,形式只扮演著內容的載體功能。藝術所要表達的內容不外乎人與他所生存的世界這兩大範疇,除了少數例外,它們長期以來便是藝術家關心的焦點。如果說,形式只是藝術再現過程中的機制,非人格化的,藝術的內容從來就不可能與人無關,即便是藝術家刻意在作品中抹除個人的個性者亦然。這是因為不論在任何情況下,藝術的生產脫離不了創作者個體的自我慾望。不論任何形態的藝術實踐,藝術家總是該實踐的主體,而它所創作的內容便是其個人自我和客觀實體的辯證結果。「自我-實體」的結合,不論以何種方式,其結果便是藝術再現的內容。「自我-實體」這一組關係中,隱藏著無限多的可能表現內容(至少理論上是如此)。在「自我」與「實體」之間,自我慾望對實體世界的投射,其所能產生的再現內容可以說分佈著無限多的,可作為藝術再現的題材與內容。其可變數的性質如下:第一,就空間性來說,所有可能的再現內容是以藝術生產者為軸心點,向外層層擴散;從藝術家的個人直覺、感覺、知覺、經驗,到社會現象、自然環境,再擴及國家現況或全球處境,這些都可以是藝術再現的內容。第二,就時間性來說,藝術家以他存在的當下時間為軸心,層層擴散,或者從歷史,或者從未來,尋找其再現的內容。它們之間的關係屬於階層化關係;亦即,從當下的瞬間、到某一個時期,再到無限大的人類歷史,都有可能納入再現的內容;從當下瞬間的存在點到永恆的無所不在,其間的關係逐層擴大,乃至於無可計數。據此,就空間性來說,李仲生對於藝術再現內容的看法,傾向於以藝術家為軸心,從藝術家的個人直覺、感覺、知覺、經驗,到社會現象、自然環境,再擴及國家現況或全球處境,都可以是藝術再現的內容。但因為他堅持以藝術家的心靈為出發點,以自動技法為手段(即直覺),去再現他所要表達的對象,因此,這樣的結果其藝術內容是無法預期的。就時間性來說,李仲生一生對於藝術再現內容有兩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藝術應與時並進,承襲傳統,並從傳統創新。第二種,藝術雖與時代有關,但因藝術是人類文明的共同表徵,故所謂延續傳統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個時代的人都必須創造屬於他那個時代的藝術,這樣的藝術並不必然要與傳統有任何關聯。要是藝術家透過直覺的再現,從中無意識地反映出傳統,傳統在此只被當成一種養份,平劇的意象在李仲生的晚期繪畫中不斷出現,當可作如是觀。要言之,平劇作為內容,指示出的李仲生在意象符號營造上的偏好,一種個性的表徵,但不代表它們是傳統的延續。第二種觀念否定了第一種的教條,正因為如此,李仲生從來便未曾積極主張過「中西融合」論,甚至到後來批評劉國松的現代水墨畫觀點是在畫地自限,提倡地域主義。李仲生的第一種看法出現於戰後初期,時間大約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亦即,李氏主張要創造「中國現代畫」的時期。在此時期,「中西融合」論仍然是民國初年五四運動的回響,情形一如1962年,在提及現代化的理想與目標時,余光中曾說的:「少壯的藝術家們必須先自中國的古典傳統裡走出來,去西方的古典傳統和現代文藝中受一番洗禮,然後走回中國,繼承自己的古典傳統而發揚光大之,其結果是建立新的活的傳統。」創造「中國現代畫」的概念屬於這一時期多數年輕一代藝術家的共同理想,其中探討的問題核心屬於前述的「符號-理想」此一範疇。李仲生的學生當中不乏附合「中西融合」論的人,其中原因容稍後再表。第二種看法大約出現於60年代晚期,在此時期,「中國現代畫」被李仲生視為地域主義,起而代之的是屬於國際性的前衛主義。現代藝術是全球性、不分地域文化的藝術。在論及現代藝術的世界性時,李仲生指出:「二十世紀繪畫思想已不是傳統法蘭西時期的拉丁民族思想,自後期印象派以後,繪畫已經成為世界性的,它可包容每一民族的藝術精神。」西方藝術自塞尚、高更、梵穀之後,它所佔有的空間已不再侷限於西方,西方藝術也從此擴展成國際的共同語言。因此,即使是一個東方人,不論它的創作媒材為何,只要他的創作符合了現代藝術的精神與邏輯(而非只是技法),其作品就屬於現代藝術。例如,李石樵雖不是西方藝術家,他的繪畫所以能夠稱為現代藝術,乃是因為在創作上李石樵遵循「現代藝術」的某些共同法則,而非僅僅由於它使用的媒材剛好是西方的油彩。李石樵用的雖是西方媒材,但其應用觀念是現代的,所以在空間上,他的作品自然不是地方性藝術(如台灣藝術),而是「國際化」的藝術。同理,當趙春翔使用中國毛筆、中國紙、及中國墨作畫,即使如此,趙春翔的畫並非中國畫,而是現代畫,理由是,趙春翔畫的鳥、竹、樹、花等等自然形象,並不在追求形似:「這些自然界的樹和竹,只是誘發他創作動機的原素罷了。」雖然使用的是中國傳統媒材,趙春翔「卻不是在畫傳統的中國畫」。因為趙春翔的畫因為符合了現代主義的美學要件—「藝術美」,所以他的畫是現代繪畫,也是「國際化的」藝術。就李仲生的觀察,在國際化過程中,現代藝術從一開始就有融合東方文化的趨勢。現代藝術不但是『反西洋傳統』,而且已經融入東方思想,原因是:「二十世紀的現代藝術,在本質上已經揚棄了西方繪畫的傳統,而與我們東方的傳統藝術思想有了銜接。」在空間分類問題上,李仲生視現代藝術已不分種族、國界、媒材、技法。因為現代藝術是在前衛藝術前導下所產生的藝術,任何人只要遵循前衛藝術的原則,他的藝術就是現代主義藝術。據此,李仲生理想中的藝術,或者說,真正有意義的藝術是否可以歸納出如下的定義:一、形式上,有價值的藝術一定不是某種幻象性的藝術,因此它必然會明顯地呈現自身的媒材本性,也正因此如此,它不可能是傳統意義上的寫實藝術。二、功能上,真正有意義的藝術因為必然不是學院的,連帶地它們必然也不可能帶有敘事性的功能。三、不論創作媒材為何,只要創作符合了「現代藝術的精神與邏輯」,這樣的作品就是現代藝術,也就是有意義的藝術。四、目的上,真正有意義的藝術不在反映自然世界,而只追求「藝術美」。五、內容上,有價值的藝術必然是國際的,不被地域文化所侷限,因此它的內容(而非題材)必須是萬邦普同的。如果上述定義是合理的,那麼李仲生的藝術價值觀可以說,其必要條件便是要具備(1)現代藝術的精神與邏輯;(2)藝術美;(3)普世的內容,而其充分條件則是要非寫實、非敘事的。必要條件中,「現代藝術的精神與邏輯」,對李仲生來說指的是不斷的創新,包括對自己風格的挑戰。然而就操作面而言,李仲生的藝術顯然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上不斷創新的現代主義,而是純度極高的超現實主義。雖然李氏不反對任何反學院的藝術,在教學上卻是以佛洛依德的心理學為基礎,認為透過無意識的自然聯想,一個藝術家的內在意象(「心象」)或精神狀態便可以自然地流露出來。李仲生的藝術價值觀與他所推動的超現實主義技法,無疑地,已在台灣美術史中,發展出一套理論與實踐具備的現代藝術指導原則與檢驗法則,我們可稱它為「李仲生主義」,它的主要實踐者就是他的學生,以及任何接受這種思想與信仰並且身體力行的人。二、李仲生藝術觀的傳承李仲生最早期的學生依循著李仲生理想中的藝術方向前進,這一批學生身分多數來自大陸,依當代文化理論來說,屬於典型的「流離群落」(diaspora)族群,在文化認同上,相信自己是中國人的後代,因而產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乃是極自然不過的事。因此,雖認同李仲生所宣稱的反學院主義的主張,在情感認同上屬於中國。例如,對東方畫會成員來說,傳統藝術特重臨摹、仿古的訓練手法,而西方學院主義又有一套經素描、寫生入手的成規。這兩種訓練均已陳腐僵化,無法造就獨特面貌。雖然如此,他們仍認為中國現代繪畫要反應時代性,具備個性與民族性,這樣的藝術,除了能獲得西方接納,又能凸顯中國文化。此處突顯的正是特定「流離群落的認同」(diasporaidentities)。(一)民族性與時代性東方創會成員蕭勤的說法最能代表這種流離群落的認同想法。他認為現代藝術具有時代性外,對於傳統元素,它需要透過個體主觀轉化為內在的真實感受,因此,「有創作性的新藝術,必然是與這個時代的生活與社會發生關係(無論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經過敏銳的感受而激發創作出來的有獨自面目的作品,此即一般所稱的現代藝術。」但是現代藝術亦可能「在其研究過程中與傳統藝術和民俗藝術發生關係」,但那絕不是死的模仿,而是「活學其精華而活用於創作的表現上」。蕭勤的說法並非特例,相反,它的說法一直是他所屬的那個世代中國人的共同願望。這不只是某種普遍的美學理想而已,而且也是某種政治主張。把這樣的政治主張付諸實現時,這個世代的中國人(特別是上述流離群落成員)所採取的策略主要分成兩派:其一是將東方傳統內容融入西方形式中,其二是運用自動技法,「透過個體主觀轉化為內在的真實感受」,經過敏銳的感受,激發創作出有獨自面目的現代藝術。前者可以五月成員為代表,後者則主要是李仲生與其學生。在上述這個離散世代中國人的觀念裡,此策略不但可以維繫了傳統文化的命脈,而且在避居的台灣藝術世界裡還可以取得創作意識上的正當性,甚至改革前衛者的光環。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何這個世代的藝術家總認為理想的藝術或真正有意義的藝術就應該如此。吳昊的自述最能說明這則願望:「我最早開始創作就用毛筆畫線條,再畫色彩,是用西方的油畫顏料,東方的想法,再融合現代的精神。」這種典型的「中西融合論」(或「中體西學論」),代表的不只是吳昊的離散世代之共同審美理想,更是其政治立場。然而本文的重點不在探討上述兩者中的「中西融合」論(即從傳統創新論),而是在分析後者的目標與策略,亦即,在於瞭解為了創作出「有獨自面目的現代藝術」,藝術家透過個體「主觀轉化為內在的真實感受」之間的實際情形。也可說,問題是,多數李仲生思想追隨者以「主觀轉化為內在的真實感受」之後,所建構出的「有獨自面目的現代藝術」,其被社會接受的可能性與實際效應。(二)個人主義首先,「獨自面目的現代藝術」這一問題可說是現代主義的形式目的論,但它並非是李氏學生獨有的主張。吳昊說:「我唯一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特色與風格」。又說:「我希望作品充滿東方的感覺,但不是表面的描繪,而是由內心的感覺發揮出來的獨特情趣,可從我畫中體會到樂觀,積極,以及生命力的衝擊,也可以感受到那充滿在作品裡得特的意象。10」早在1951年即拜李仲生為師的蕭勤(1935-),他對「獨自面目的現代藝術」的處理方式是迂迴的。以他1994年的《大限外之17》為例,作品上的「光」來自許多筆下的大量「留白」,「留白」被視為中國傳統水墨畫的重要特徵之一,也是光意象的具現方式之一。此種留白對蕭勤來說不但是製造光的策略之一,也是中西融合的一種嘗試。1958-63年,從李仲生研究現代藝術的梁奕焚(1937-),他的「獨自面目」如藝評家MargaretMoose說的是一種:「獨有的藝術形式,既非東方,亦非西方,既不現代也不傳統,而是超越時空,無始無終卓越的人間性。」此外,1957年與梁奕焚、陳文夫同時從李仲生學畫的鐘俊雄(1939-),也強調個人之繪畫語言創作,詮釋「生命」之意涵,或表現東方女人的獨特之美。總之,上述自述中,不論是「自己的特色與風格」、「留白」、「既非東方,亦非西方」或「個人之繪畫語言」,都道盡了李氏學生對於創作「獨自面目」的深切渴望。1、非思(unthought)其次,在技法方面,「主觀化的內在真實感受」這一問題雖可說是現代主義的創作方法之一,但確實是李氏學生普遍認同的技法。吳昊說:「我畫畫有一個想法,就是不希望受別人的影響,儘量讓自己的想法呈現出來」,指的便是這種沒有預定觀念的技法。這種非預設風格的技法,蕭勤的說法是:「我並不是想在畫作中直接表達對於生命的力量與能量,只是感覺透過我而傳達出來,我擔任著一個媒介的角色。」蕭勤為何要這樣畫,答案是:「我也不曉得,這是一種潛在的能量。」這種說法在霍剛的自述裡,有一個比較清楚的定義。霍剛(1932-)是在1951年跟李仲生習畫,他認為:「藝術是一個人內在精神創作的產物,藝術家是在任何環境之下仍能保持不變的內在,保持童稚的心靈。」他在其《無題》(2001)的創作自述中說到,「我的畫不管構圖、符號,是一種象徵、一種啟示。我使用的技巧是為了達到精神的心靈空間,一種對人類及宇宙的萬物無限嚮往的情愫。」面對他的作品時,霍剛建議觀者,「不要有任何成見,捨去求知、求解的態度,過濾思維,用心靈去體會,去感受。」反過來說,創作者其實也是以相同的態度在面對他的藝術創作。例如,1952年隨李仲生學習現代藝術的朱為白(1926-)即自承:「藝術創造不能脫離自身生命特質,將自我特質融入自我創造思維欲求,藉某一生活有的獨特媒材,創造出『真實』的自我藝術語言。」1951年開始從李仲生學畫的金藩(1926-),在述及創作《節日的歡騰》(1998)時提到這種把個體「非思」帶進創作行為的道德價值:「抽象性的表現,感受是人文社會具體特定節日,而如平日化在藝術家所要的主觀美好可能性,以數十年的變與不變固定在畫作的系列中」。2、自動性技法藝術家創作過程必然經歷某種將主題客體化的心理建構過程。對李仲生的門人而言,這個過程主要是透過自動性技法所達成。1953年至1955年從李仲生先生研習畫論的焦士太(1929-),從李仲生力倡的「潛意識自動性作畫」觀念中得到啟發,走向現代藝術創作,認為:「『真』是藝術的源頭,是生命原我的呈現,是內心世界的剖白,沒有了「真」,便失去了『美』。」他的《巴黎印象》(2001)則是「希望將人鮮活的生命溶入畫中,傳達出心理真實的聲音!」誠然,李仲生學生往往強調這種過程是某種程度上的無意識(包括部分的與完全的),而其結果可以是「入渾然忘我之境,沉醉於如錦璀燦的心靈之美,是我心所感,我心所悟」(劉芙美),也可以是「表現自己當時的精神層面及內心的情緒。」(黃潤色(1937-))王慶成(1948-),1974年入李仲生畫室研究,聲稱是以「自動技法素描寫實突破圖案之設計,雙重影像不協調、不合邏輯、不對稱呈現畫面,不重複之心象潛意識,讓畫面空間無限擴張延伸。」每一個學生或許皆有獨特的藝術面貌,但自動技法卻是他們共同的創作手段。以自動技法揭露潛意識心象的情形並不僅於上述學生,例如1968-75年入李仲生畫室受教的朱麗麗(1948-),至今畫中出現的符號,皆為其個人「心象」所造之心象,目的在「探索自身內在感官心質、心勢、心韻、心趣等能動力之『無限性』。」1969-84年入李仲生畫室研究的程武昌(1949-),指出其《作品1995》(1995):「出自自己內在感動為形式,把不相同內容元素,以自動性使其元素有生命的能量,而成有機體,…使時間在畫面上延續,用線來貫穿、壓縮、縱橫畫面使精神空間更為呈現,獨一無二的心靈語彙構成一個密閉與外界無關的心靈世界。」許雨仁(1951-)則說:「在創作中,唯有訴諸自由解放的思維,那個『真實的自我』才敢『暢所欲言』和『為所欲為』,而『自主性的創作』和『個性化的風格』,也才會水到渠成的出現。」又說:「我的素描隨時隨地都可進行,材料不拘、形式不定、內容也沒有預設,雖然如此,有一些圖形似乎隱藏在本我心之中,在我無意識/無目的的塗寫活動中,就會自然自動地出現。」而許輝煌(1937-)則自述其作品《心象世界》(1983)是作者「以無意識的筆觸將其潛意識揮灑出『聯想性』的心象世界。」自動技法的優點對1965年入李仲生畫室研究的詹學富(1942-)而言:「繪畫創作是個最可自由的耕地,去除學院法則及現實自然的限制,轉由本能非理性的自由伸張,千萬變化於焉產生。可臻自由自在繪所欲繪,無限開闊的繪畫領域。」自動技法顯然是李仲生最吸引學生的地方,它解放了任何創作章法的限制。人的心靈用來充當藝術創作的被動平臺,這個概念並非出於李仲生的原創理論,而是法國超現實主義運動的導師布荷東。而李仲生是經由藤田嗣治的指導,接受此理論並加以實踐與發揚光大。1976-82年入李仲生現代繪畫研究室的陳聖頌(1954-),他的說法正是此概念的寫照,他說:「近年來我的作品,大都是以自己對南台灣的自然景觀的關注,或於陽光的變化或關心於自然及生態等等,皆為創作的原始動因。」雖如是,他的作品絕非南台灣的自然景觀的直接模寫,而是心靈的「印象」所自然流露的「心象」。鄭瓊銘(1948-),1979-84年入李仲生畫室研究,他的《大地寓言》(2004)也不是任何一處自然的寫照,而是某種「心象」,「是採半自動技法,藉著短暫強烈的創作靈感,以豪放暢快的創作方式,傳達出潛意識裡不停歇的筆觸,…舖設出壯闊的場景,同時映照出作者的成長背景與生活經驗的點滴。」為了完全成為被動的印象平臺,1980年,入李仲生老師畫室的原來(1962-)認為:「創作本來就要真性情,存在一個無私無執的心境,才能夠悠遊於筆墨之間,也才能夠真正地去享受創作所帶來的喜悅感。」三、李仲生主義的審美理想與現實誠然,李仲生生前的教學與論述主要在現代藝術生產的形式上,對於藝術收受的問題甚少提到,至於藝術的功能與目的對他來說則似乎是自明知理。在90年代之前,國內從事現代藝術創作與評論的人,似乎普遍存在著藝術家只管創作就行,觀眾是否能夠接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無創新,創新才具有歷史價值,才是藝術家真正關心的事情。這種以創新為唯一職責的想法,李仲生師生也無例外。至於李仲生所認同的藝術之功能與目的,或許許輝煌的一段自述最能闡明李仲生的觀念:「我的創作…展現出非文學性、非敘事性,純繪畫性的前衛繪畫之風格,…沒有可視性的世界條理,卻有非可視性的世界條理,加上些中國畫的幽雅線條,以及富有戲劇性的東方神秘色彩而構成『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神秘而奇幻的心象世界。」簡單說,藝術的目的就是要創造某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這樣的作品對一般人來說,充滿「神秘而奇幻」。就像多數的現代藝術家,李仲生所傳授的藝術價值觀與創作方法,前者是一種理想,後者在創作方法上堅持以「無意識」為技法乃是現代人特有的思考形式。現代思想詢問的是「我思」(cogito)如何能處於「非思」(unthought)的形式之中。例如,既要思考造型藝術的存在,又要思考個人生命的存在,這便是現代藝術家不同於古代藝術思維之處。在古代的藝術再現中,藝術家個人生命是隱蔽的,他的存在屈從於他所使用的造型語言之下;在思考再現物的世界時,藝術家與他的非思,界限分明的。但在現代藝術裡,藝術家總是在創作之際,思考著要如何連接、表明和釋放那些足以表現他個人的存在之語言或概念;換言之,他試圖將他的我思與非思串聯在一起。既要再現物的表像,又要再現藝術家個人的存在,這便是現代藝術家所面臨的問題。也正因為如此,現代藝術在符號語言之間,便充塞著過多藝術家的生命,以致於圖像的意義總是私秘的,無解的。當人們試圖在創作之際,思考著要如何連接、表明和釋放那些足以表現他個人的「存在」之語言(或概念)時,他事實上是要將他的藝術品當作他自身「存在」的見證,而不是要抹去他的存在的)。然而,誠如1980年入李仲生畫室的陳威宏(1965-)在其創作自述所指出的:「思考『存在』的意義,當下存在的只是『正在思考』!」。我思與我的存在不能同時並存;古老的笛卡兒定理-我思故我在,在此應改寫為:我思在我不在處,我在我不思處。然而,現代藝術家卻勉強要兩者同時存在於他的藝術中,這便造成了溝通上的無解。對於多數李仲生的學生而言,下列聲明仍然是真實可信的:「藉由心可感的媒材,不拘泥的表現方式,創作出來具個人面目的作品,才是有價值的創作行為和結果。而它是能適用於很多人的美感經驗,且被接受的。」(施淑,1962-68年之間於李仲生畫室習畫)。李仲生的學生深信,任何媒材,透過最不加修飾的個人藝術語言,就能完整表達我的「不思」,而我的「不思」與「個人藝術語言」能適用於多數人的美感經驗。這其實是一則美學上歷久彌新的老問題,那就是「真實」的自我藝術語言與「真誠」的表現意圖,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前者的「真實」是由後者所保證?或者是後者的存在必然可以產生前者?的確,這則詭論長期被創作者所忽視。正是在這樣的認知下,我們更應該關心李仲生主義的審美理想,其假設前提確實存在著難解的問題。結論綜觀李仲生一生所堅信的藝術價值觀,包括他認為有意義的藝術必須符合現代藝術的精神與邏輯-不斷的創新,包括對自己風格的挑戰,不以模仿自然為務,而是只要創造「藝術美」,這種美必須是具有民族性與時代性,但又是普世的美。為此現代藝術必須放棄學院寫實,放棄敘事功能。在創作技法上,李仲生則認同超現實主義所主張的自動性技法。在審美理想上,藝術家應以創造『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神秘而奇幻的心象世界為己任。在審美理想上,「李仲生主義」確實是某種現代化的神秘主義,這與他所主張的再現技法有著結構性的關係。它之所以被稱為「神秘」,並非由於宗教或民族特性,而是技法上的自動性,最終必然導致藝術再現的自傳化、個人化、私密化,並進而導致溝通上的困難,尤其是抽象性藝術更是如此。反之,具像類藝術則雖也有自傳化的可能,但因任何可辨識的題材必然存在著某種文化意涵指涉,因此仍有溝通的空間。在李氏的學生當中,江漢東(1929-)、鐘俊雄、黃步青、李杉峰(1950-)吳梅嵩(1955-)、林鴻銘屬於此類型,雖然超現實的成分與外觀仍然十分明顯。
基本資訊
- 原始資料連結
- 資料來源
- 主題分類
- 建檔單位
- 地點名稱員林/彰化女中
- 緯度23.9618/24.0809
- 經度120.571/120.544
- 地圖
本網站使用Cookies收集資料用於量化統計與分析,以進行服務品質之改善。請點選"接受",若未做任何選擇,或將本視窗關閉,本站預設選擇拒絕。進一步Cookies資料之處理,請參閱本站之隱私權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