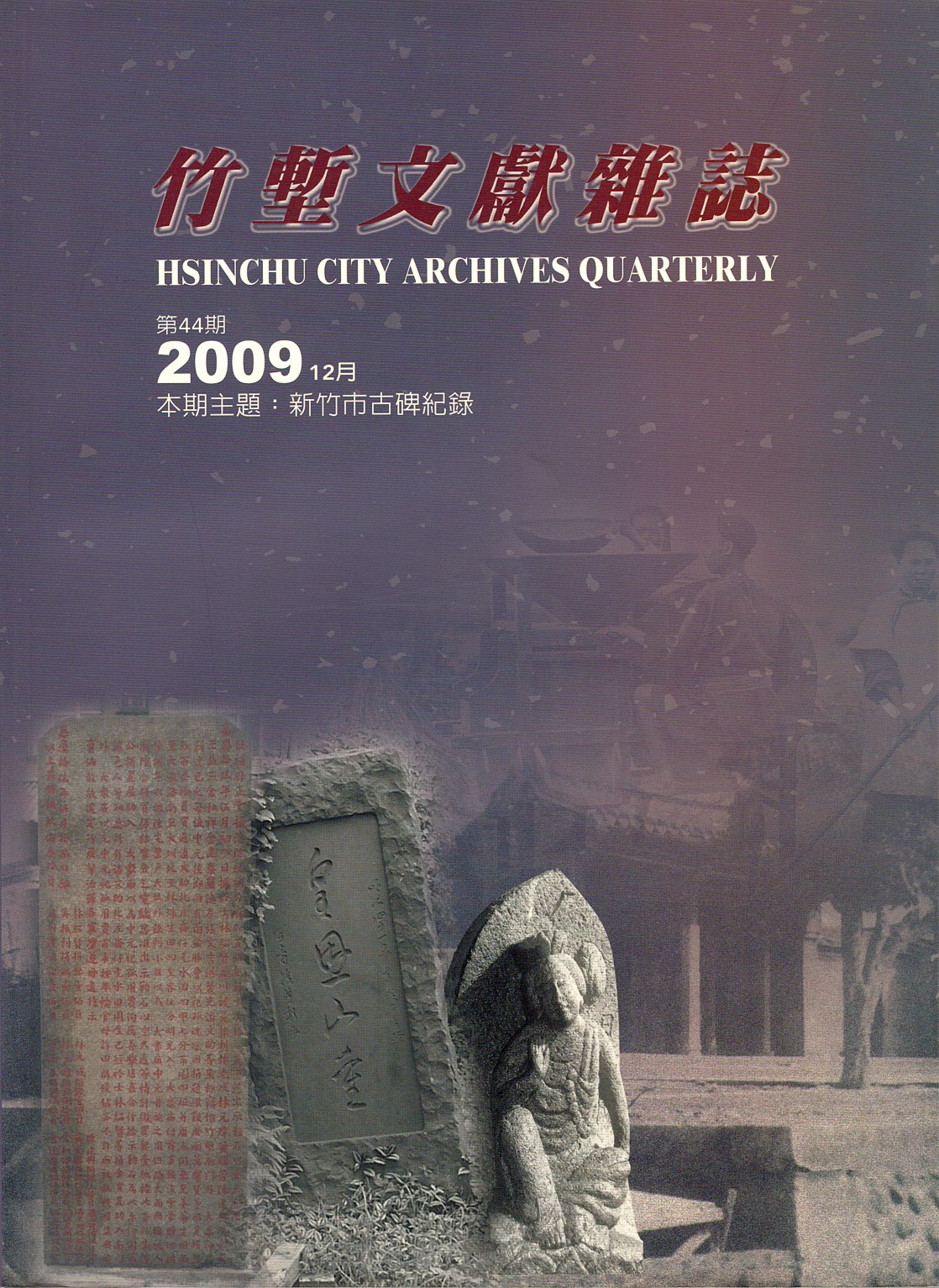編輯報告 台灣自明鄭以來,無論官憲示禁,諭令頒發,寺廟整置,城池興築,街市建造,宗祠設立乃至史實敘述,大多立碑碣以存其事。因此,碑碣中所記錄的也就是台灣史地沿革、政經發展、社會宗教變遷等各方面的重要史料,是研究區域社會發展的重要參考資料。 竹塹城是淡水廳廳治所在,是大甲溪以北的北台灣政經文教中心。保存碑碣的數量也蔚然可觀,自有其淵源,成為探討新竹區域發展的重要文獻,從已有的石碑內容分析,竹塹城地區的水利建設,大致在乾隆三十年代,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在此之前,草萊初闢的移墾社會,不利於立碑,乾隆二十一年(1759)廳署移駐竹塹後,官署及官祀廟宇的修置,道路津梁的興修、政令官諭之頒立,道光九年(1829)築城之後,吏治整飭,風俗督正等相關的碑碣記載,反映出新竹地區的風貌。 陳朝龍《新竹縣採訪冊》(1895)輯錄了清代治台時期,新竹地區重要的碑碣,由於採訪較為詳實,是探討的重要來源。日治時期以來,由於政治的因素,官署、官祠的大量拆除,以及都市計劃下的土木建設,使得石碑受到極嚴重的毀損,石碑本身亦因長期風雨剝損而破壞。1986年,邱秀堂的《台灣北部碑文集成》,為求完整收錄清代碑文原碑己失者,即以《新竹縣採訪冊》所載,據錄成文。為新竹地區的石碑做了詳盡的整理。 1998年刊行的《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新竹縣市篇》。其體例以現存碑碣為主,1981年為斷限,輯錄新竹市石碑45件,未拓(基本資料)約95件,現存者或有闕漏已遺失之碑碣未錄,於研究者頗有不便。 碑文內容紛呈雜陳,運用時應與文獻相互參酌,如〈大眾廟中元祀業碑〉指出文獻上建廟年代錯誤;〈新建長和宮水仙王殿碑記〉之「同治伍年歲次乙丑獵月」年代則前後矛盾。〈重修長和宮碑記〉直接指明「竹塹郊奉前廳憲諭始建造長和宮」;〈重修竹蓮寺捐題碑記〉則將同治、光緒、日治三個時期,捐題人士集聚一處而以同治十二年視之,因而模糊廟宇歷史意義。援引碑碣,自應臨淵履冰,謹慎將事,避免考訂不確,強行論斷。 以往有關石碑的論述大多為單篇文章,意有未盡或僅就碑文重加敘述,並作必要的說明,鮮少以碑文內容為研究對象。因此以碑文的內容考訂,史實增補,史事輯錄,呈現較可觀的區域社會發展全貌,正是本期嘗試的起步。
跳到主要內容區塊
:::
竹塹文獻雜誌第44期編輯報告:新竹市古碑研究
基本資訊
- 原始資料連結
- 資料來源
- 主題分類
- 建檔單位
- 管理者新竹市文化局
- 撰寫者新竹市文化局
- 創作者張德南
- 時間資訊出版日期2009/12
- ISBNISSN10287329
- 媒體類型圖書及手冊
- 出版者新竹市文化局
- 存放位置新竹市文化局
- 地點出版地點新竹市北區東大路二段15巷1號 (120.9681945, 24.8114733)
- 檔案授權
受著作權法保護-僅限於本平台有限度公開瀏覽
- 地圖
本網站使用Cookies收集資料用於量化統計與分析,以進行服務品質之改善。請點選"接受",若未做任何選擇,或將本視窗關閉,本站預設選擇拒絕。進一步Cookies資料之處理,請參閱本站之隱私權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