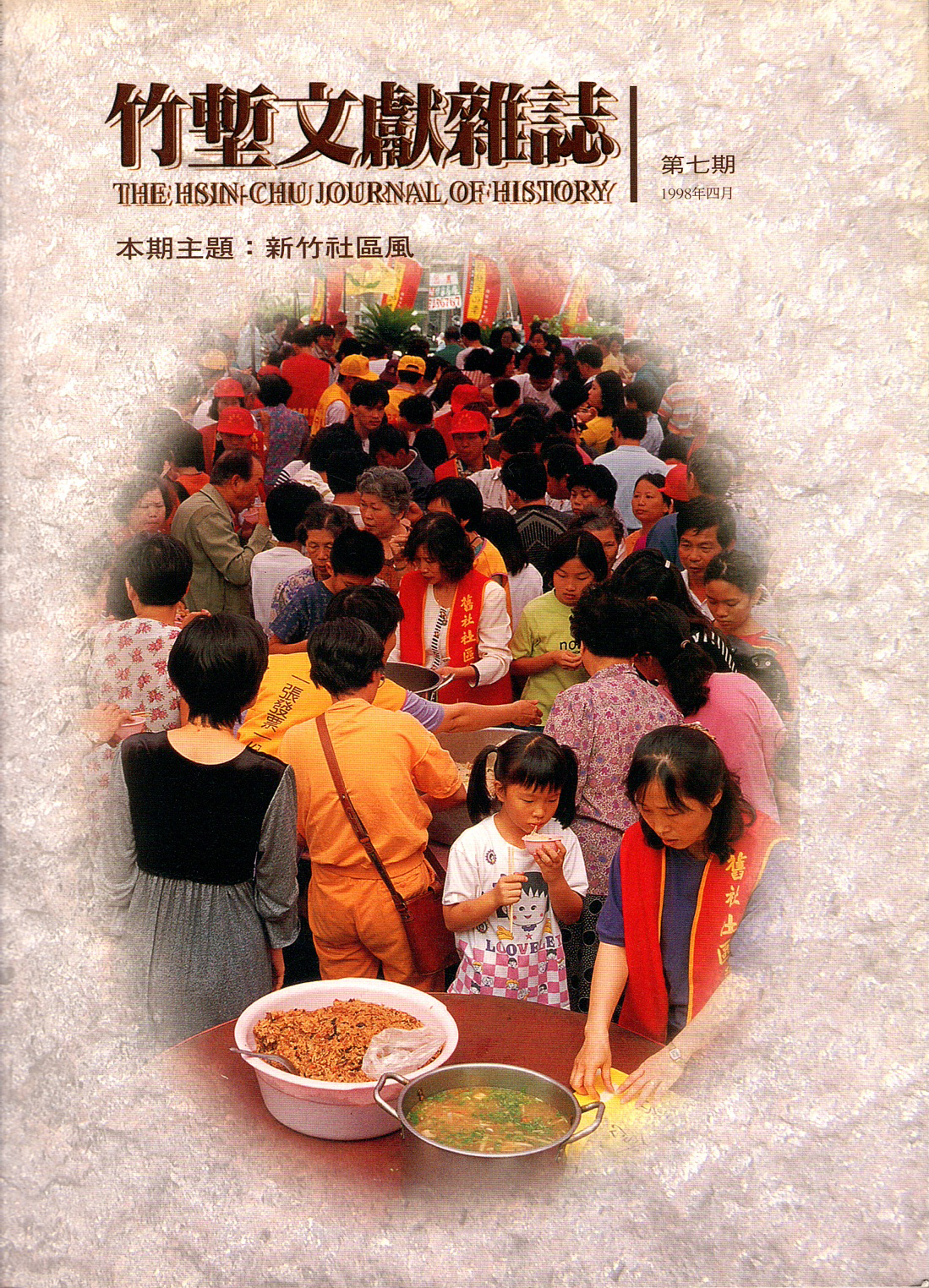若以基層行政單位的部分自治作為社區的標準,早在1935年日本殖民政權下的首次市議會員與街庄協議會員選舉開始,台灣就已進入社區的時代。1965年至1982年社區發展作為一種政治經濟機制,1982年至1992年為社區政策的模糊時期,文化經費被削減。社區工作被收歸中央的情勢越來越明顯,1994年社區總體營造在全國展開,社區作為一種文化與意識型態機制。但社區總體營造的誕生雖有其文化紮根的意義,卻為執政黨在選戰危機中鞏固政權的霸權策略之一,社區發展協會的設立無法執行文化政策,反而被政治勢力佔為己有。舊社能獲選社區總體營造的專案試點是由於台灣僅有的八座節孝坊,其中三座在舊社,成為重要的地方特色,另外沒有嚴重的派系對立。在社區總體營造過程中,改變了舊社社區人們民主參與習慣。雖然社區仍以家父長體制為主導,可是舊社在條件限制下,社區居民、特別是女性與青少年的參與,突破了過去社區頭人對文化事物的壟斷,而社區又沒有因為舊頭人與新義工潛在的衝突而分裂,成為一個有趣的案例。
跳到主要內容區塊
:::
營造瓊樓玉宇還是海市蜃樓?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歷史與個案的分析:以新竹市舊社社區為例
基本資訊
- 原始資料連結
- 資料來源
- 主題分類
- 建檔單位
- 管理者新竹市文化局
- 撰寫者新竹市文化局
- 創作者林宗弘
- 時間資訊出版日期1998/04
- ISBNISSN10287329
- 媒體類型圖書及手冊
- 出版者新竹市文化局
- 存放位置新竹市文化局
- 檔案授權
受著作權法保護-僅限於本平台有限度公開瀏覽
- 地圖
本網站使用Cookies收集資料用於量化統計與分析,以進行服務品質之改善。請點選"接受",若未做任何選擇,或將本視窗關閉,本站預設選擇拒絕。進一步Cookies資料之處理,請參閱本站之隱私權宣告。